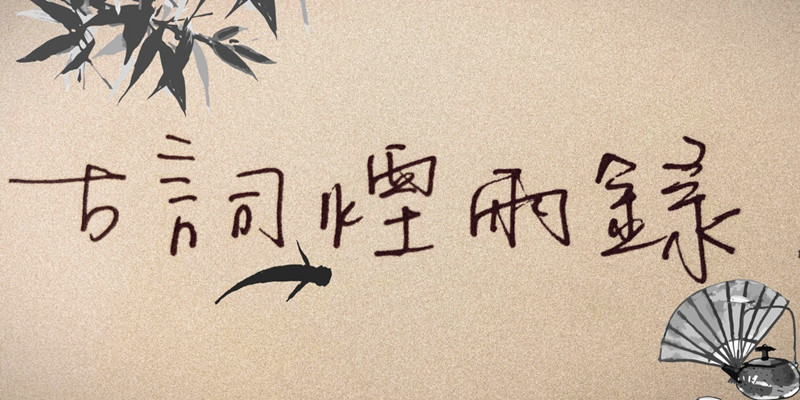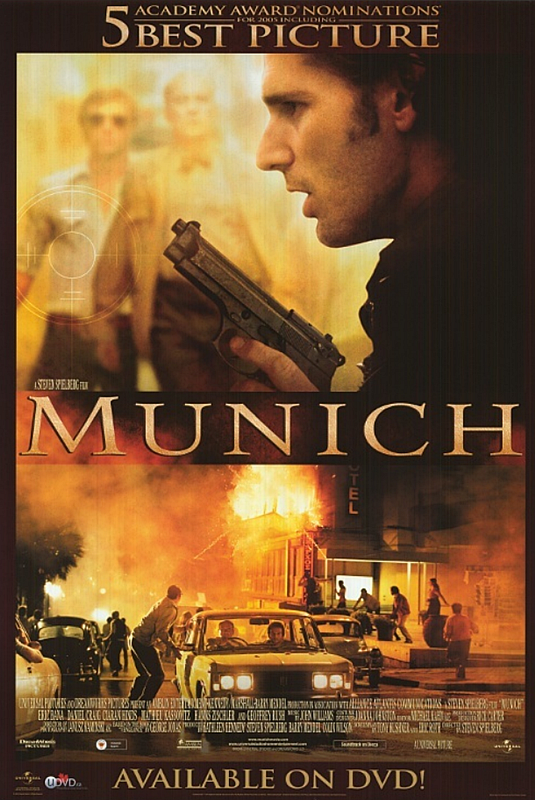其实,神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传道书 3:7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这样一段沉默的时期感到惊讶。神有权创造声音,也有权保持沉默。他知道两者的完美时机。
沉默的起点是玛拉基的终章与历史的断章。
玛拉基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在他的书中,神向祂的子民重申了一个熟悉的主题:祂爱他们,渴望与他们建立需要顺服的关系,向他的子民讲述了一个熟悉的故事。他爱他们,渴望与他们建立一种需要他们服从的关系。但他们拒绝服从,他们通过滥用圣殿和向他献上低于他们最好的东西来表现出不敬。以色列民拖欠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玛拉基书3:8-10),甚至“用言语烦琐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烦琐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玛拉基书2:17)。当上帝指出他们的罪时,他们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反驳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玛拉基书3:8)——用借口掩盖悖逆。
玛拉基书3:17可能是随后沉默的关键。神厌倦了与子民的“无效对话”——他们拒绝承认罪,反而用争论和借口逃避责任。在整个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的对话本应是“责备-悔改-复兴”的循环,但在玛拉基时代,这一循环彻底断裂:他们不再回应祂的呼唤。
旧约的最后一个声音,止于先知玛拉基的呐喊。公元前430年左右,玛拉基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废墟旁,向悖逆的以色列民发出最后的警告:“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玛拉基书 4:5-6)
此时的以色列,早已不是所罗门时代的黄金国度:圣殿虽经以斯拉、尼希米重建,却沦为交易的市场;祭司们敷衍献祭,将“瘸腿的、瞎眼的”牲畜献给神(玛拉基书1:8);百姓口称“耶和华”,心却远离祂,甚至质问:“公义的神在哪里?”(玛拉基书2:17)
玛拉基的预言如同一记重锤,敲碎了以色列人最后的侥幸。当神的责备不再被接纳,当“辩论”取代了“顺服”,神厌倦了听到他们的争论、自我辩解和借口。他厌倦了几个世纪以来与他的子民来回奔波之后的话语。在整个旧约中,上帝和他的子民一直在进行对话。上帝确切地告诉以色列人他们需要做什么来取悦他并维持他们的关系。以色列人曾服从一段时间,但最终,他们开始跟随假神并做出其他不服从的行为。然后,上帝会赐予他们艰难的时刻,使他们从悖逆中悔改并归向他。他们服从了一段时间,但循环又开始。在玛拉基时代,当神再次指出他们的罪时,他们不仅没有悔改,反而指责祂是问题所在。
神选择了沉默——不是遗弃,而是退后一步,让历史的洪流自行冲刷出祂预备的道路。
神是否生气,给了人类 “沉默的待遇”?在他的儿子耶稣出现之前,神是否允许了一个节拍,就像一首伟大的协奏曲中的戏剧性停顿一样?在这一点上,神没有选择解释。因此,人们对这段时间的理解,大部分是基于对神的品格和他如何运作的了解而做出的猜测。
新约的第一声,则在四百年后响起于马太福音的序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1:1)这声宣告看似突兀,实则是沉默的回响: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呼声(“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马太福音3:3)正是玛拉基预言的应验(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马太福音11:14);耶稣的家谱不仅连接亚伯拉罕与大卫,更串联起以色列四百年间的苦难与盼望。
沉默的四百年,历史的书卷褶皱中都藏着哪些秘密呢?
这四百年并非“空白”,而是神书写的“预备篇”。
新教所说的两约之间时期(又称“400沉默年”),在天主教和东正教被称作次经时期,是原始正典和新约之间的时间段。它被认为涵盖了大约 400 年,从玛拉基的事工(约公元前 420 年)到公元1世纪初施洗约翰的出现。它与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 516 年至公元 70 年)大致相当,涵盖了希腊化犹太教的时代。
新教说的沉默期,是因为在那段时期没有新的先知兴起,上帝也没有向犹太人透露任何新事物。许多被天主教会和东正教接受为圣经的次经书籍都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许多伪经作品、圣经伪经和犹太伪经也在这时出现。对两约之间时期事件的理解为新约提供了历史和文学背景。
但这一时期也有一些重大事件,主要有:犹太侨民和希腊化犹太教的起源;第一座犹太教堂建立;圣经通用语言从希伯来语到阿拉姆语和希腊化希腊语的变化;马加比起义的事件;哈斯莫尼王朝和希律王朝的统治,随后是罗马的统治;希腊语《七十士译本》问世,这是希伯来语圣经首次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死海古卷》的写作,其重新被发现成为现代和当代圣经研究的核心等。
而且,在玛拉基及以后的时代,波斯帝国统治犹大(公元前539-332年)。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允许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以斯拉记1:1-4),却也埋下了文化交融的种子——波斯的神祇观念、行政体系悄然影响着犹太人的思想。随后,亚历山大大帝的铁骑踏碎波斯帝国(公元前332年),希腊化浪潮席卷近东。希腊语“科伊内希腊语”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旧约被译为希腊文(七十士译本),犹太哲人斐洛用希腊哲学诠释摩西五经,这些都为后来保罗用希腊语传教、福音跨越文化壁垒埋下伏笔。
公元前63年,罗马共和国吞并犹大,庞培的军队踏入圣殿庭院。罗马的统治带来了道路网络,如“罗马大道”,带来了和平,却也加剧了犹太人的反抗情绪——奋锐党、匕首党等激进组织崛起,圣殿的权柄被罗马任命的祭司长架空。当耶稣在伯利恒诞生时,罗马帝国表面的“和平”之下却暗流涌动,而这正是神所允许的时候(加拉太书4:4)。
其次,在动荡的时局中,犹太教内部催生了多种纷繁复杂的思潮。以圣殿为中心的撒都该人掌控宗教权柄,却日益世俗化;法利赛人严守律法,却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艾赛尼派隐入昆兰社区,用严格的禁欲等待末日;而奋锐党则用暴力反抗罗马。这些派别之争,本质上是“神应许的弥赛亚究竟是谁”的争论——有人期待军事领袖(如马加比革命),有人盼望律法师,有人渴望神圣的改革者。
正是在这种态势中,以色列民对弥赛亚的期待愈发迫切。死海古卷(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发现印证了这一点:昆兰社群的文献中反复提及“义人受苦”“末日审判”,并引用但以理书的“人子”异象(但以理书7:13),将弥赛亚描绘为超越天使的“神圣者”。四百年的沉默,让“神的儿子”不再是模糊的应许,而成为刻在犹太人心中的“必然”。
沉默四百年,神为何“闭口不言”?
面对沉默,人们常陷入两种极端:或质疑神的信实(祂是否忘了我们?),或强解神的意图(祂在惩罚我们)。但圣经的线索提醒我们:神的沉默,是爱的智慧,是历史的节奏。
时间对上帝来说是不同的——一日,在神那里就是一千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后书3:8)。四百年对我们来说太长,而对上帝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音乐小节的长度,足够休息。
对我们来说,没能经常思考沉默。而上帝为了许多目的会将静默编织到所有受造物中。沉默给人提供平静和反思的机会。沉默可以集中注意力。我们期待在死亡之后保持沉默,在权力面前保持沉默。我们在虔诚的敬拜中保持沉默,当我们因为痛苦或绝望而走到尽头时也会保持沉默。
玛拉基书2:17记载,以色列民竟说:“凡作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当罪成为“合理”,当悖逆被粉饰为“智慧”,言语的责备已失去效力。正如父母面对沉迷手机的孩子,反复劝诫无效后选择暂时沉默——不是放弃,而是让孩子在后果中醒悟。神在两约间的沉默,恰似这种“痛苦的克制”:祂退到幕后,让以色列民亲手触摸罪的代价(被掳、分裂、压迫),直到他们从走投无路时发自内心的喊出:“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历代志上 16:35)
还可以把旧约先知比作前奏,新约的基督才是“终极乐章”。神的沉默,是为了让“道成肉身”的真理不被先知的余音淹没。正如管弦乐队在演奏协奏曲时,会在高潮前稍作停顿,让主奏乐器的全貌震撼全场——四百年的沉默,正是神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预备的“寂静时刻”。
沉默,作为神的“看不见的手”的作为,表面上的“沉默”,实则是神在不动声色的引导。波斯允许重建圣殿,是为保存犹太信仰的火种;希腊化带来语言统一,是为让福音跨越地域;罗马的和平与道路,是为让“好消息”快速传遍万邦。正如但以理书中的“泥上印印”(约伯记38:14),每个帝国的兴衰都在书写“末日将近”的伏笔。神的沉默,是祂在“幕后掌权”的明证——祂从未离开,只是以更隐秘的方式成就旨意。
沉默给予我们有哪些启示呢?
两约间的四百年沉默,不仅是历史的片段,更是信仰的镜子。它提醒我们:当神不说话时,我们是否仍能持守信仰?以色列民在沉默中分裂、挣扎,却仍有以斯拉、尼希米这样的“余民”坚守律法;中世纪千年虽有信仰混乱,却也孕育了修道院的抄写传统。沉默不是信心的终点,而是“凭信前行”的起点——正如约伯在失去一切后仍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记19:25)
其实,不只是这四百年的沉默期,后来耶稣出世,也有过多次的沉默。当他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面前,面对咄咄逼人的文士和长老时,他不言语(马太福音26:63),当大祭司逼问他为什么都不回答时,他依然“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马可福音14:61),他不是软弱,而是对“父的旨意”的完全顺服。我们的生命中也常有“沉默的时刻”:祷告未蒙应允、努力未见果效、爱未得回应。此时,我们需要像以色列民等候弥赛亚那样,在沉默中等候神的时机——“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加拉太书4:4)
神的沉默从未等同于“冷漠”。四百年间,祂仍在历史中工作:兴起外邦帝国、保存宗教文献、预备救恩的道路。同样,我们的“沉默”不应是冷漠的旁观,而应是主动参与——像施洗约翰那样“预备主的道”,像初期教徒那样“在逼迫中传福音”,在生活的细节中活出“基督的样式”。
两约之间的四百年沉默,是神写下的“间奏曲”,是历史的长镜头,更是信仰的启示录。它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有时如洪钟(旧约先知),有时如耳语(新约福音),有时则如寂静中的心跳(两约之间)。但无论何时,祂的爱始终如一——祂在沉默中预备,也在沉默中兑现应许。
当我们在今天重读这段沉默的历史时,或许应该问自己:我们是否在忙碌的属灵活动中忽略了神沉默的呼召?是否在“追求即时的回应”中失去了等候的耐心?愿我们能在沉默中学习信心,在等候中培养盼望,因为那沉默的尽头,终是“哈利路亚”的颂赞。
又一片寂静即将到来。在末世,启示录 8:1 说,当羔羊打开第七印时,天堂里寂静了大约半小时(二刻,half an hour)。这种沉默是在上帝对那些在地上违抗他的人释放他的审判完成之前。它位于最后一章之前,上帝将毁灭降临在地上,然后被救赎的人与他一起享受新天新地。
我们应该倾听上帝说话。但是当他停止说话时,我们真的应该注意。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悔改的机会,并为接下来的事作准备。我们最好反思上一个400年的沉默,并在下一次沉默到来之前,现在就跟随耶稣。
根据相关资料编写,2025.7.14-17
相关阅读:两约之间的历史(史料)
信仰与见证文选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