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二卷,是我人生道路上跳跃式的快速转折期。
父亲早逝,母亲苦苦支撑着一个破败的家,我在寻找出路,先是投亲无门,靠人介绍进了国民党军汽车厂,当了学徒工。好在很快迎来了解放。正值时代剧变,我这个农村孩子有幸地走上了阳关大道:在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行列里,参加了进军大西南的伟大战役。不但有了落脚地,还生存发展了下去。
在解放军队伍里,新组建的汽车部队,千万里长途奔驰,接受着人民军队的阳光雨露;在全新的经历和教育中,生活变了,观念和思想感情,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我幼稚、无知。面对一切新鲜事物有巨大的兴趣,对汽车技术知识有着“儿童般的喜爱”,凭借较聪颖的天分,因喜爱而较为勤快,一路上,接受着崭新的教育,也赢得了师傅们的好感,受到较好的关爱。
进军大西南的整个战役,基本上是走到哪里解放到哪里,汽车运输军需物资,常处在第一线战场的较后部,一般不直接处在战火之下。我们的连队生活,主要是紧张的运输,无休止的日以继夜的长途奔跑。
我所在的是汽车连技工班,任务就是保障全部车辆的安全运行。在长途跋涉中,从江西、湖南,弯向福建、广西,最后到达贵州省。整个大行程,多的是高原和群山峻岭,车辆本是收集敌军的各种杂牌车,车祸事故多,抢修技术活多,车辆保养维修多,我们技工班的任务繁重劳累,好在我有幸生活在一个较为优秀的小集体中,师傅们技术全面,
个个是技术精英,而且他们相互团结友爱,还有个好班长。
从杭州到贵阳,在艰辛劳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全新的经历中,历时有年,我终于病倒了,医院检查确定为肺结核(可能是父亲的传染)。
到贵阳住下了不久,领导决定要我复员,但这时又遇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不但没有复员回家,反而辗转调入了贵州军区机关,后来还破格被提升为干部。解放,不但给我带来了新生,还有连连好运。这就是第二卷的基本内容。
第一章 寄居
到舅公家去
父亲临终时的嘱咐,家庭生活的困窘,使姆妈决心把孩子送出去,到外边去寻找活路。姆妈叫我去舅公家,在这个阴霾的家里似乎透出了一丝阳光。姆妈说,那是一棵大树,可以倚靠的。为这个大事,还为我做了一件新衬衣,这着实让我高兴了好些日子。
舅公叫华挺生,是姆妈的娘舅,我叫他舅公。我还听姆妈说过一个神奇的故事。有一年,有人要抓他,家里来了好多人,楼上楼下都翻遍了,就是没找到人。全家都乱成了一团,只有账房先生在那里坐着纹丝不动,一直等到那些人走了以后,账房先生变成了舅公。
真神了。而我竞要去舅公家,去见那个神话里的舅公,因此特别向往和憧憬。
舅公家住在方家井,在县城西边20里的山区。那天,我是跟着姆妈坐汽车一起去的。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汽车,更是第一次坐汽车,因此我很兴奋,老远就听到汽车轰隆隆的响声,站在上面感到非常惬意,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我还踮起脚尖来,尝试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
车很快到站了,但下车还要步行走一段才能到方家井。
方家井距离大姨妈家欢坞里不远,有几里路吧。姆妈先领我到了姨妈家。姨夫姓陆,是个大地主。据说那边山里凡是能见到的土地山岭都是他家的。一走进他家门,姨家的小儿子走过来迎接我,这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小表弟主动跟我一起玩,让我看他新买的自行车一一这种东西我也从没见过,只是在小源的货栈里,见过一个车把手和一个
轮子,那是房东一辆坏了的自行车的剩余零件。表弟还领我走进他的房间,那里有很多好玩的摆设和用具,还给我吃糕点水果,玩得很开心。不久时,姆妈招呼我离开,下午要到舅公家。“这里不是你玩的地方”,姆妈小声对我说道。
到舅公家时,已是傍晚了。大台门进去,天井厅堂,房子很气派。舅公舅婆都是大块头。舅公高大一些,是一位威武的汉子,看上去年纪不是很大,见面很热情;舅婆也是五大三粗,嘴巴特别宽厚,也很能说话。
晚饭的菜肴很精致,各种荤菜素菜都是小碗小碟的,他家有好多人,可饭桌上只有我们四人吃,都是大人,我就显得有些拘谨,吃完饭后,我帮着收拾碗筷。
到舅公家后,我一直惦记着姆妈说过的话——舅公答应我做家庭寄读生,以后有机会去读书或者到外边去工作。舅婆说,她曾培养过一个小孩,后来出山了很有出息。听了这话,我明白,到舅公家里来,是我母亲为了解救我们一家,这是安置我的重要一步。
舅公多年在外地,具体干什么不得而知。他在接近解放时突然回到家乡来,而且在县城里有时还发表演说,德钧叔就听过他演说,“他讲话声音洪亮,很有说服力。”到第二年,他又到县城去开米店——我也就成为那家米店的学徒——由这些行为有人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不过在我印象中,他更像个书生。解放前夕被派回家乡浙江富阳地区来,做迎接解放的工作,也许是真的。听说后来他在上海定居。
舅公真的具有书呆子的特性。他在家也不做具体事情的,有时一个人下棋,一下好半天,无论是在乡下还是在后来的县城米店里,他都不随便出门。
舅公从外地带回一个女子,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小孩长得虎头虎脑,很可爱,挺像舅公。由于大舅婆没有儿子,这个男孩就跟着大舅婆,小女人被完全养起来了,守着空房。不过,据我所知,她私底下与长工阿怀是有关系的,他们时常说些悄悄话,透过木板壁,我在房间里悄悄听到的过。
这位小媳妇,对我没有好气,因为她不能差遣我做事。我虽然是个乡下孩子,看着她无权照管自己的孩子,也有点可怜她。有时她在我面前作态,我知道这是她发泄的一种方式,也就没有太多的反感。
她作为小老婆,却跟长工好,感觉她不像是个正经人,不过,我喜欢阿怀哥,也就不在意他们的悄悄话。
舅婆叫王琢如,曾经做过乡长。舅公长期不在家,因此这个家是舅婆主持的,舅婆很能干,经管着家业,有田地,也有石灰窑,还做大米生意。我因此也熟悉大米加工房的生产活计。
另外还有一位老人是后外太婆,小个子,圆而白净的脸上,有一只半瞎的眼睛。她也收拾得很干净,一双小脚,只在家里转,只管厨房灶里,从不出大门,也不过问其他事。这位老人很会支使人,很会调度我去干活。她会笑着说,阿林你说园子里有没有可摘的熟瓜呢,要有的话今晚大家可以吃上一顿,其实意思就是让我去园子里摘些黄瓜来,晚上要吃,她这样说了,我再劳累也得去跑一趟的。
除了阿怀是里外一把手的长工壮劳力以外,还有一位小厨娘,叫阿花,当年也就十六七岁吧。她特别勤快地劳动,干活利落周到,她自己也特别讲卫生,对我还有点特别的注意和帮助。不过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位小厨娘有特别的厌恶,好像是厌恶她太热爱这份当佣人的活计似的。
舅婆没有儿子,却有一位千金,叫幼娟,在上初中,跟我同年,而且住在楼上楼下同一间房间,但我跟她没有一句话可讲,大概这与身份和年龄有关吧。我甘心当劳动力,也不用讨好谁。幼娟不去上学时,在家里就是闺房不出,少不了要老阿太和小厨娘伺候的。
去舅公家的当晚,大人们交谈了一些有关我父亲的话题,比如“阿环怎么就没有一点积蓄呢!他可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啊!”舅公这样说着我的父亲,顺手拿来一本课本,笑着叫我过去说,你来解读试试。我念着课文,一边胆小地解读着,课文上有一句话“鱼贯而入”把我憋住了,我不会讲。但其他的文章我基本都讲清楚了。
“你和我家的幼娟的情形差不多。”舅公这样评论着我刚才的讲读。“先在家学习一段时间,以后有机会出去上学还是找个工作,看看再说。”舅公这么说,我母亲听了很满意的样子。后来姆妈对我说,幸亏没让你写字,你的字写得太难看了。
所谓寄读
姆妈又住了一天就要回家去了。临走,到我住的房间里,我的房间只有一床一桌,实际上是楼梯间的一角。她再一次理了理我的书桌上的书本和纸张,说了句“好好学习”,再也无话,带着离别之情,姆妈走了。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其实我一天也没有读书,也没有上课,或者与幼娟表姑共同学习。至于找工作,舅婆也曾有话说,舅公生性不求人,为你的事也曾经写信托人但都无回信,也就没办法了。
前后有半年的时间里,这里出入着一个十足的小长工。我这样一个半大不小的穷亲戚,实在正好补缺,一个小劳动力,一个小听差。
家里要服侍的人不少,要干的活又太多。好些时候,我还要跟着长工阿怀一起干活,烧石灰,从出窑到装缸,样样都干,出密不久的烘灰还烫手,每次都呛得鼻子出血,眼睛直流泪。碾米,要到外村去,米场里飞扬着漫天糟糠,看不清对面人的脸面,噪音让人听不到说话声。挑担,我很难撵上大人们的脚步,过去没干过这样正经的活,经常是虚汗连身,干咳不断,有时甚至痰中带血,累得过头了,整夜睡不着觉。
干力气活过去在家里是有的,不过都比较轻微,而在这里是与长工比肩干,有时还招来别人的笑话。比如挑担子,那一次有人给我装好了一担菜,看上去好像能挑起来,但走不多远就吃不消。阿怀总是告诫我不要上当,少挑点,多走几步试试,有把握了再挑走,他说:要记住有句老话,百步无轻担。这阿怀,倒是总是处处关心我的。
在家里,衣服脏了姆妈会拿去洗,在这里,衣服脏了只会招人嫌弃,说你邋遢,告诉你该自已去洗衣服了。
不久,舅婆跟我说,要冷了,先回家去吧。过一段时间有别的活计再叫你来,再来。
不久后,姆妈又让我回到舅公那边,不过这次是到县城江边,舅公开的米店,做学徒。
舅公在富阳城里开米店,我做学徒。还有一位学徒。在这里,我体会到了吃别人家饭的滋味。舅婆还多次数落我,对我干的活挑毛病:“阿花不见人时就放心,她肯定去干什么了。你就不一定了!”后来我还是回到灵桥老家了。
初冬,我就穿着姆妈临走给我的新衬衣作为外罩回家。那件衬衣我是第二次穿,其实我里面还穿着旧背心,那背心太旧,太破了,我只好把衬衣穿在外面,看上去还是蛮漂亮的。船上有邻居叔公见我这样冷的天穿着白衬衣,就问:“你不冷啊,这样冷的天只穿单衣。”姆妈乍一见我这样穿法很诧异,但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看到了她的眼泪,姆妈看我一眼,只说了声:“回来就好。”
舅公家的两次经历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就凭心而讲,他家里正需要一个小工,只是给我个工作而已,至于寄读也实在并不现实了。
一个人离开父母,在哪怕是亲戚家,也得不到任何怜悯,还是要用自己的劳动去抵偿。我品尝着人生的第一堂课,给我能回忆的,只有失落和怅然,体会到人世间的凄凉。
还是回家来了。
阿林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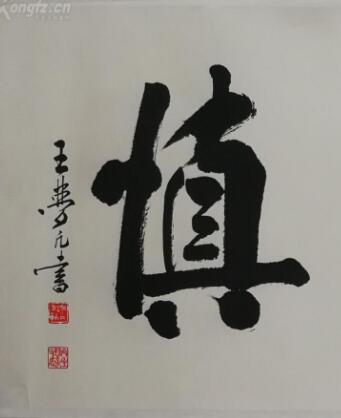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