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作代会召开于1984年12月,贺的提议见于张光年1984年2月25日的日记,今即以1984年为准,看看孙犁一年中的作为。
北方的1月,照例是严寒,12日,孙犁复函潘之汀,给潘看稿,告以有几篇已转《天津日报》。
1月19日,在王勉思、杨坚寄赠的《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的书衣题字,记下了“中午食鸡,碎骨挤落一齿”的琐事。
1月22日,写读书记《买〈魏书>〈北齐书〉记》。
1月23日,复函老友吕剑,谢吕赠近作《一剑集》等。
2月2日系甲子正月初一,旧历新年,15日,在小胖赠送的《达夫书简》的书衣题长跋,述论郁氏的爱情及命运,精辟深刻。
2月16日元宵节,复函韩映山,谢所赠小说集《串枝红》及照片,透露“春天出门”的打算。
2月23日,做小说《葛覃》,记一位坚守底层,默默无闻,“创造不息,恪尽职责,求得命运的善始善终”的故人。
3月4日,写短文《谈印象记》。
3月4日,做小说《春天的风》,内容为开导一位贸然登门,“文革”中患上精神方面疾病的女青年。
3月7日,做散文《戏的续梦》。
3月17日,为即将创刊的《农村青年》杂志,写《文学与乡土》短文。
3月20日,写短文《谈简要》。
3月28日,做散文《昆虫的故事》。
4月6日,做小说《一九七六年》。
4月10日,写《读小说札记》组文讫,对莫言、李杭育、关鸿、汪曾祺、古华、张贤亮、铁凝等的近作,做了认真的评论。
4月12日,写短文《小说与题材》。
4月13日,写短文《小说与三角》。
4月23日,写回忆文章《移家天津》。
4月27日,做散文《父亲的记忆》,这一天“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
4月29日,做小说《小D》。
4月30日,复函韩金星,谈稿子。
5月2日,写散文《唐官屯》。
5月7日,做《红十字医院——病期经历之一》。
5月19日,写读书记《买〈饮冰室文集〉记》。
6月1日,写读书记《买〈崔东壁遗书〉记》讫。
6月23日,做《散文的感受与含蓄——给谢大光的信》。
7月份,似未动笔,大概因三伏大暑太热。夏天,孙犁自述,在他居住的那个越来越乱杂的大院儿,“每天晚上,我不开灯,一个人坐在窗前,喝一杯凉开水,摇一把大蒲扇,用一条破毛巾擦汗”,夜深,有了凉意,才钻到蚊帐里去。
立秋以后,8月22日,致函张金池,就《孙犁著作年表续编》,提出一点看法。
9月7日,复函杨栋。
9月11日,复丁玲长函。
9月12日,做《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评贾平凹的小说等。
9月14日,读书记《读〈伊川先生年谱〉记》完篇。
9月15日,写读书记《读〈朱熹传〉记》。
9月17日下午,写读书记《读〈宋文鉴〉记》。
9月21日下午,写短文《谈笔记小说》。
9月22日,致函田晓明,嘱数事。
9月28日凌晨4时,做《病期经历·小汤山》,同日,复函韩映山,谢韩之公子大星刻赠的印章。
9月30日凌晨3时,做《病期经历·青岛》讫。
10月6日下午,做《病期经历·太湖》。
10月10日,复老友李准长函。
10月14日,复函杨栋。
10月15日清晨,写《谈读书记》讫。
10月20日,长函复李贯通,孙自认为这是他1984年中“最有感情的一篇文章”,“因为在这封信里,倾诉了一些我早就想说的话,借题发挥了我平时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和想法”。
10月22日,写短文《谈赠书》。
11月24日,复函杨栋,谈文稿。
11月28日,致函王蒙,谢赠书。
11月30日,写短文《谈通俗文学》。
12月10日,复函冯立三,强调读书的重要。
12月31日,公历年的最末一天,孙犁写信二通,一给姜德明,一给李贯通,均谈书论文。
以上,我不厌其繁地以“编年”的形式,罗列了孙犁1984年全年的文字生涯。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读书记、书信、题跋,量多而质优。准此可知,当京华诸公为作协的领导人选而各动心机之时,古稀之年的孙犁则置身事外,心如止水,沉潜书籍,多读深思,笔耕不辍,佳作迭出。孙犁在京老友甚多,不排除有人将这一内部消息透露给他的可能,看他夏秋之际的言行,似乎也正是针对这一“传言”而发。他向报社编委会和市委宣传部提出,辞去报社和天津作协分会的所有职务、名义,要求离休。丁玲将要主持创办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他表示“非常高兴,要尽一切力量为它服务”,但坚辞列名编委,因为“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想)集中剩余的一点精力,写一点东西”。
对自己的身体、性格,孙犁有着清醒的认识,1983年编毕《远道集》,他告诉来拿书稿的编辑:“写到疲倦时,则两眼昏花,激动时则手摇心颤。……有的是因为感情用事,有的是因为考虑不周,得罪了不少人。”丰富的阅历,读过的大量古籍,使他对文人从政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那些狂喊着怀才不遇的文士,真的委以重任,却又大多难有建树——自身或亦不免,还是以不蹈覆辙为是。退一步讲,即使“全国作协副主席”只是代表一种荣誉,不需要真的登堂视事,对这种荣誉,孙犁也早已看淡,他在10月份给李准的信中写道:“至于名利是非,弟青年时代或有此念,今行将就木,已完全淡然。……今足不出门庭……深以此钝根天生为苦耳。”1985年6月,他写了一篇《官浮于文》,对文艺界争官儿的实质看得很清楚:“它是名实相副,甚至实大于名。官一到手,实惠也就到手,而且常常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至于自己,当然会洁身自好,不去蹚那浑水。孙犁晚年能够写出十本足以传世的不朽之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2013年春于崂山西麓秋河草堂
原载金陵《开卷》2013年第12期
计纬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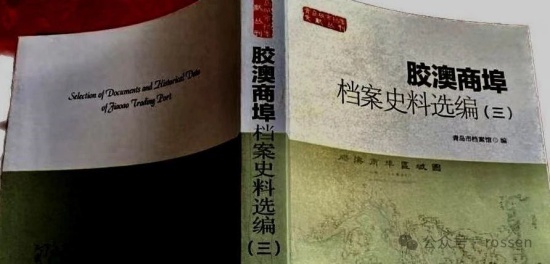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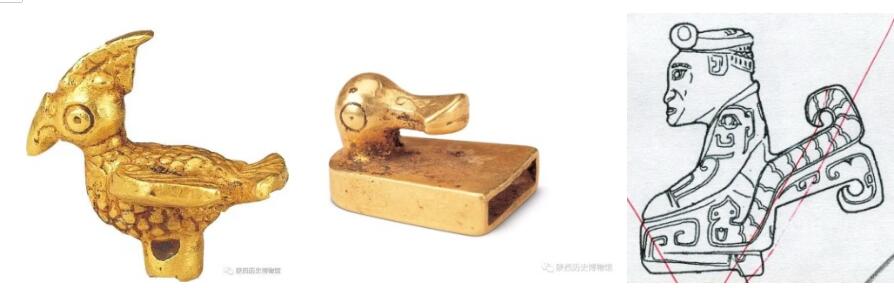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