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眾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畦留夷與揭車兮(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艸乞輿。五十畝為畦也), 雜杜蘅與芳芷(杜蘅、芳芷,皆香草也。言己積累眾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蘅,雜以芳芷,芳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峻,長也)。願俟時乎吾將刈(刈,獲也。草曰刈,穀曰獲。言己種植眾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絕,落也),哀眾芳之蕪穢(言己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眾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眾賢志士失其所也)。
段意:把自己培植集結衆芳,暗比聖君之招致并擢用眾賢,哀嘆衆芳蕪穢,是説眾賢(尤門客)多變節而叛己。本段句子雖少,涵義卻深,須細細品味,與第二段比較,方能得其大旨。這是本文忠臣悲劇的第二次展開。
作者:觀其接納衆芳,雖亦似劉安;而從以聖君自期看, 必劉正則也。
要點:“雖見放流” 聖君與衆芳(組喻)萎絕與蕪穢
17 雖見放流
此語有點令人發笑。王逸注曰“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眾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試問屈原若在放流中,如何能頗爲大規模地植蘭種蕙,簡直成了種花專業大戶了。可見 “放流” 云云根本無其實事,最多可勉强喻為被王疏離、不復在權力中心的狀態而已。也許有人會認爲,放流云云,王只是順便説説罷了,不足當真坐實用來推理。筆者則認爲,連楚屈原者本人都不存在,所謂其“放流”,更根本為子虛烏有,而絕對是假的,不過王逸故意用此種語言形式一點一點地提示其假而已,至於全部認假。整部《楚辭章句》中有白紙黑字直接説明這一點。下文編輯者假屈原的名義説的話才是真的。其實王逸常用解釋某事的機會,故意漫不經心地把另一件事否定。
18 聖君與衆芳(組喻)
屈原大量滋蘭樹蕙,王注謂 “種蒔(即種植)“眾香”(=眾芳),勤修仁義,朝夕不倦”。他還種植留夷、揭車、杜蘅、芳芷等多種芳草,王注說,這是 “積累眾善(即衆芳), 以自潔飾”,使自己“芳香益暢, 德行彌盛”。又補說道,屈原自己種植衆芳,是“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等待天時而將收獲、收藏這“衆芳”并且盛宴款待它們,酬賞他們的功勞。說着說着,漸漸清楚露出了比喻的内容。簡言之,這位屈原與前代聖君一樣招聚眾賢。對比前文(第二段) 所言君王褒有聖君純德,能舉用衆賢(衆芳)而達於至治,其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句,乃明說 “眾芳,喻群賢。“往古夏禹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眾賢,使居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而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後又注説 “蕙茝皆香草,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眾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是雜用眾芳之效也)。從以上原文及《章句》中可看出, 這裏有一組比喻。
不但“衆芳”比喻眾賢人,還以衆芳生長之天時暗比聖君臨治的天時、以滋蘭樹蕙比喻培養選拔賢人(門客),而且以“獲取收藏”香花比喻招集延攬賢才于麾下以備用,以“饗其功”比喻根據各人績效論功而行賞等等。一句話,這些文字所表達的意思是,“屈原”本人以治世的聖君自許,而招聚啓用賢人。編輯者看似無意,其實有心,竟然是尊屈原(而且認爲屈原也自信)爲堯舜禹湯文一樣的聖君。這,自然可證實《離騷》首段的家系、生日、名字之内美及及作者之絕遠修能,其實都是天生聖君的稟賦和資質, 而且可與《遠遊章句》中顯露的 “自傷不(能如舜)值於堯”的悲傷互證。所以這位也被叫做屈原的神秘人物,幾乎自視聖君。我們在 “屈原賦二十五篇”中,將多次發現各種類似的暗示。
王注中 “言己種植眾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意思是“説自己種植多種芳草,希望有幸讓它們枝葉茂盛生長,果實成熟,願等待天時,我將收穫它們收藏它們,并且對它們論功行賞。用這些話來説,君也該積累蓄養衆多賢人,根據不同的時機提拔使用,并且期待他們崇仰支持自己的治理”。此話中的 “言君” 從上下文看,當然和前一句“言己種植眾芳,……吾將獲取收藏而饗其功也” 中之“言己”、 及“吾” 所指者是或几乎是同一人,至少是同一種人。弄清前句的主語代詞己、吾,對比補充句中的主語“君”,從語義上講,前後這幾個代詞互相等同應已毫無曖昧。從以上所言聖君蓄養眾芳過程的一組比喻看,王注早已悄然將屈原與聖君等而同之。
19 萎絕與蕪穢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 。從比喻的實義看,屈原多種眾芳,即公然培養很多才俊之士,這在昏暴之君看來算不算集結 “黨人” ? 這恐是很危險的。竊以爲,在乾綱獨斷的制度下,為臣者即使唱贊歌不合暴君口味,或者初時還算合其口味,後來變得走調不合了,也有性命之憂;何況竟然自詡聖君之選?再看看此處屈原對自己所培養的“眾芳”是什麽態度呢?衆芳若有未待收獲而枯萎早夭者,於屈原應無傷;他悲哀的是,衆芳枝摧葉爛,失香變臭啊。也就是説,人不幸一般性地死(枯萎死亡)了,不足讓我傷心,但是變心、失節、中傷、賣主求榮等行爲(蕪穢),就太令人悲傷了。話已説到這個份上,王逸又掩飾性地補充說,屈原是説自己憑藉修行忠信,希得君王任用,卻遭斥責貶棄,“則使眾賢志士失其所也”。好像考慮眾賢志士失去依靠,更勝過關心自己;而他所謂眾賢士,其實很可能被暴君當作黨人。話已差不多說清了,還試圖回頭再掩蓋一下“屈原”的非凡臣身份,如此閃爍其詞,王逸真煞費苦心啊。其實, “蕪穢”只是 “眾芳” 處於高壓下的常態。
第四段 老之將至 修名是立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厭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也。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妒。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妒。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眾人所以馳騖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眾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七十曰老。冉冉,行貌。恐修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修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誌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
段意:黨人追名逐利、嫉妒賢人,我獨急於仁義,將以餘年建功也。自言獨急於仁義而異于衆人,後文將此發展到絕對的高度,自是編輯手筆。但强調雖老而愛修名,卻是劉安的特點。
作者:劉安,被編輯改動過。
要點:獨急於仁義 老冉冉其將至 恐修名不立
20 獨急於仁義
接上,既然眾芳萎絕蕪穢,則舉世滔滔、盜名趨利;唯屈原一人,獨急於仁義,恐修名不立,已達到光榮的孤立,所謂舉世皆濁我獨清也。這是脫離塵俗社會的、理想乃至幻想之道德高度,是自高自孤乃至自絕於君主專制社會必然導致的自殺,自是因忠昏君、愛亂國,救其國全然無功所導致的絕望的自殺了。顯然,這是編輯設計楚屈原形象的重要步驟,爲其凄壯之死預做鋪墊。
21 老冉冉其將至
這不是一個五十嵗以下的人説的話,也未必就是近七十嵗老者所言。 所謂 “七十曰老”,是誤導性年齡;而東方朔《七嘆·怨世》“年既已過太半兮” 之王注 “言己年已過五十”云云故意説得不精確, 但可當作有助考証的數據(是劉安的年齡)。以年齡論,此人當係劉安(前179-前122年)。而“真正”的屈原、即劉安之太子劉正則(前162-前122年)平生未達到“老”。
22 “恐修名之不立”
王注 “屈原建誌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 云云,可參《漢書·淮南王劉安傳》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戈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 《史記·劉安傳》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 。所以,在劉安父子皆留文《楚辭》的前提下,“恐修名之不立” 竟也成了可用以辨別劉安的一個特徵。
第五段 所行忠信 以自率厲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華也,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蕊。動以香淨,自潤澤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長顑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常顑頷,饑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眾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攬木根以結茝兮(攬,持也。根以喻本)。貫薜荔之落蕊(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蕊,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己施行,常攬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索胡繩之纚々(胡繩,香草也。纚々,索好貌,言己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芳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顔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于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懟而自沉也。《反離騷》曰“棄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之心哉!
段意: 自謂多服食、攬用諸芳草,使形、神合道,生命品格得到提升。自己這樣做,是“上法前世遠賢” (不知何人),雖所得忠信不合時俗,仍願以彭咸投水自勵。其實又是一篇忠臣悲劇論。
作者:從主旨看,是在暗示性地描摹那個忠楚投水的虛假人物屈原,所以這段文章屬於編輯者,即自劉向至王逸間有名或無名的楚辭編輯者,不排除部分字句借用了我們所謂“淮南資料庫”。
要點: 飲露餐英 遍攬群芳 所行忠信 法夫前修 彭咸遺則
23 飲露餐英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二句,王逸先粗解作 “旦飲香木之墜露,暮食芳菊之落華”,後又因朝為正陽、夕為正陰,朝夕亦為旦暮,乃換說之,成“旦吸正陽之津液”及“暮吞正陰之精蕊,并且用 “動以香淨,自潤澤也 ”作結,意思是動輒(經常)攝取木蘭芳香、秋菊精華來潤澤自己身體和精神; 這似是服用了一種高效能藥膳;而吸正陽、吞正陰云云,分明是攝取天地之精華的一種修行,與食菖蒲、餌靈芝等借服食而求仙之行徑也相同。王逸繼續解釋下句説,只要“使我形貌信而美好” (原文:信姱),并且“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原文:練要)。雖常消瘦,忍飢不飽,亦何所傷病也(原文:長顑頷亦何傷)。“何者?眾人苟欲飽於財利,己獨欲飽於仁義也”(原注又附加此句,意思是:爲什麽呢?衆人確實在金錢名利上貪得無厭, 只有我想在仁義道德上達到圓滿完足啊”)。看來芳草鮮花(眾芳)在此處的含義變了; 它們不再喻賢人,而成了一種藥餌, 而且是提高個人道德品貌的妙引。所以屈原强調自己每日飲蘭食菊以求形净神澄而近得道,爲此何惜身體清癯(當因服藥膳而辟穀造成)。這,似乎把 “求仙” 的“進步” 當成道德修養的提升了。服用良藥能使人容光煥發而形貌也美好一些,應是合理的;但能使人形貌 “信而美好”,“信” 與後面“美好”用連詞 “而”等立地連起來,是忠誠、誠信意,吃什麽仙丹靈藥能使人連形貌都變得更忠誠、值得信賴呢?有點不可思議,果然很神。王逸何故好像有意把話説過了頭,先別同情,值得琢磨。
24 遍攬多芳
由服食芳木鮮花之精華推廣,攬木根、貫薜荔、矯菌桂、索胡繩等對香草香木的處理操作,依王逸說,就有了 “據持根本” 、 “執持忠信” , “矯直菌桂芳香之性”、“善自約束”等正己正人、修德建功的作用。王逸解釋得很辛苦。但把服食求仙、進藥膳,以及把玩香草香木的效果與個人心性和道德的提升關連起來,就不令人信服。例如把“攬木根”解釋成“攬木引堅,據持根本” 即堅持根本大義,已很牽强(簡直還不如手握一根鐵棍或抱一個樹根更堅强或有根氣)。把 “貫(薜荔之)落蕊” 解釋成 “蕊,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也令我們起疑: “執持忠信”竟是什麽樣貌?蕊,竟等於“實”(這應是故意出個小錯,以引起讀者考究),在任何別處也找不到證據來坐實此解。把“蕊” 解成 “實” ,再把“果實”的“實” 變爲“誠實”、“忠實”之“實”,所以“貫落蕊”才解作“執持忠信貌”—這就是王注的解釋之邏輯。換一句話說“貫落蕊”貌,就是“執持忠信貌”了。也許因看到王逸解不通,五臣注此句云:“貫,拾也。蕊,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结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 (《昭明文選》卷三二)—把“蕊”解成“花心”而表屈原忠正不偏之心,好像比王逸之解合理一些,但仍難真通。質言之,“遍攬多芳”從修辭上講雖可象徵取得一些美好的德行,也可有助增强外觀美乃至心靈美,但把它和道德修煉、政治行爲乃至堅持忠信的樣貌扯到一起,是荒唐的。把“累香草之實”當作一個形象來象徵主人公之美好而忠實,已很勉强;把它當成一種獲取忠誠並用以事君的模樣乃至手段,就講不通了。王逸似認真而不露行跡地解出或做出的“執持忠信貌”,也放任讀者愛聽不聽、愛悟不悟,但其實竟是對屈原之忠誠的一種嘲弄,雖然連屈原形象也是包括王逸本人在内的編輯們平白創造的。
25 所行忠信
王注所云 “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仍閃爍其意。細察 “己所行忠信”之特別措辭,其中代詞 “所”,是用來復指動詞“行” 的賓語“忠信”的,也就是復指前文解“貫薜荔之落蕊”得到的、所“執持”的“忠信”的,上文“所執忠信”,即上文所貫“薜荔之落蕊”;但即使“薜荔之落蕊”可比喻“忠信”,它作爲喻體當然不能代替本體“忠信”的;喻體一代替了本體,就產生了滑稽而扭曲的反面效果,就像說”這個蘋果如珍妃的臉”一樣漂亮,或者“太陽就像他”一樣偉大,都產生反諷效果。
所以,此處的“忠信”可疑可議,乃是對屈原(無其人)式忠信的暗示和暗諷(其謬)。以下簡稱忠信A。因爲楚臣屈原其人本是子虛烏有的,編輯者特別選擇這樣的比喻方式來相配地描寫他。此處屈原所行忠信與前文所持忠信,我們稱之爲忠信A,是貫徹《離騷》始終的。
26 法夫前修
由服食和把玩芳草香花而達到(?)自善、修德、建功、求仙,据作者自言,這是 “法夫前修”而“非世俗之所服”,即不是今時俗人所信服和遵行的。所謂前修,依前解“修”之例,王逸解釋爲“前世遠賢”, 猜測是指傳説的三皇五帝或其賢臣、也隱約涉及王子喬、韓眾、羡門高等所謂得仙者,皆籠統而言。但我們卻鮮見有前修依靠擺弄香草立德立功立言的。另外,以前修為法,是把眼光回看古代來尋找榜樣,對任何社會或政治改革乃至道德自律,都是無益而“不周於今世之人”的, 又何能奏其功。而屈原和彭咸二位雖是我們今日能確定的前修,卻也都是極難捉摸的人物,更談何效法!除非不問情由、人云亦云地胡亂充當他們的粉絲。
27 彭咸遺則
如果沒有屈原這個人,哪裏會有他要依循的彭咸之遺則!末句 “願依彭咸之遺則 ” 王注說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卻不提 “彭咸”見於何書,自劉向至王逸的漢儒成功編輯《楚辭》以來,至今也一直無人有根據地考出“彭咸”究屬何方神聖、或他是否真投了水。至於杜撰的姓屈名平字原的人則根本未曾存在過,則其投水更是玄而又玄、無中生有。 對此,完全未讀懂王注,也未真研究《屈原列傳》,洪興祖就用他的《補注》專橫而且絕對自負地說,屈原 “于頃襄之世”之前若干年,當懷王時做《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从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懟而自沉也”—妄信屈原蓄死謀已久、幾十年前決心已定、就計劃好了自殺,這是何等的不近人情!他還引《反離騷》“棄由、聃之所珍兮,摭彭咸之所遺” (抛棄許由、老聃珍貴的自由生命而撿起彭咸傳下的投水行爲)並評論説 “豈知屈子之心哉!” 好像唯有他知屈原之心!
第六段 忠信繫累 九死不悔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難也,言己自傷所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沉江,是謂多難也)。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繫累也),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繫累也,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既替余以蕙纕兮(纕,佩帶也),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眾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誌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
段意:只因履行忠信, 遭讒陷被廢棄而遭拘縛,雖太息自悲,卻爲此九死不悔。當然,這又是一篇忠臣悲劇論,越演越烈,形勢急轉直下。似乎將近拐點了。
作者:編輯者,詞句多取自淮南資料庫, 或有更改,加上有導向的《章句》注釋。
讀者會發現王逸《章句》解釋經常完全超出《離騷》原文。有時故意在好像無關緊要處大做文章,有時故意采用錯誤的解釋方式,有時竟解出匪夷所思的内容,總是要以種種細節堅定地表現自己所知的“屈原”之特別身世經歷和爲人, 并且極其小心地把真假屈原區別開來。本段中履行忠信部分,是繼續宣揚楚假屈原的忠德;而“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繫累也”,應是透露蓼太子之遭遇。 即使在一段之内,相鄰的句子中作者也時或把真假屈原故意混淆起來說,來挑戰讀者的辨識力。
要點: 民生多艱 為人所繫累 “蕙纕”與“攬茝” 雖九死其猶未悔
28 民生多艱
“民”,亦遠非今日所謂人民也,因雖稱“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下,説的卻是申生、子胥等之枉死,所以句意最多是哀王族或貴族枉然盡忠者之民生多艱也。又,伍子有掘墓鞭楚平王尸事,此處 “屈原” 引之而不諱,是不以伍子爲逆也,與屈原對所謂楚君所執可疑可議之忠信正合,不必更爲之辯。
29 為人所繫累
對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二句,王注曰“言己雖有絕遠之智(解修字),姱好之姿(解姱字),然以為讒人所鞿羈而繫累也(解鞿羈二字),故朝諫謇謇於君(解謇朝誶三字),夕暮而身廢棄也(解夕替二字)。把 “修姱”二字分別解為“修能”之“修”和“姱美”之“姱”,就有用心(尤其“修”字之解。提示此處的“屈原”有“絕遠之能”而應是那位蓼太子)。又以人對馬的羈勒(鞿羈)推及讒人對己的“繫累”,總感有點牽强附會。《孟子.梁惠王下》:“若殺其父兄,繫累其子弟,毁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其中“繫累”也和“繫獄” 意思相似。如果“鞿羈”解為“繫累”,再解為“拘縛”乃至“繫獄”,王逸是否要傳達因“好修姱”(效忠問政)而“繫獄”(拘禁)的意思?下文接言 “朝誶而夕替”,即早晨剛剛向君王進諫,晚上—在極短時間内—就遭廢棄了,似是加强和證實了拘縛、乃至“拘禁” 的含義。這當然指真屈原被集體屠殺之前的被“繫獄”(或拘禁);看來,王逸在一串解釋的末尾很不明顯的地方,説出了一點真實:真屈原(蓼太子)被殺前曾遭“繫累”。
30 “蕙纕” 與“攬茝”
如前解,“蕙纕” 與“攬茝”即“帶佩眾香,行以忠正”或“履行忠信”意。“帶佩眾香” 放在“行以忠正”之前,從比喻的角度來看,竟也是把喻體視作與本體并列甚至更重要。“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誌彌篤也”,也是喻體先於本體的例子。所以也應記爲“忠信A”,現在“忠信A”很諷刺地成了“屈原”被構陷入罪的原因,於是他就發誓說,自己如此執行忠信, 是我心之所美所善,因此受讒、被君王斥責加罪,支解凌遲、粉身碎骨死N次,也不後悔。不知其底細者聽來,真忠君愛國屈大夫之誓言也。知道底細者再深究之,則更知編輯者又在變幻人、德之真假,仍暗携諷意。
31 “雖九死其猶未悔”
王注“言己履行忠信,……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支解,根據《淮南子·人間》“商鞅支解,李斯車裂”語及注,也作“枝解”、“肢解”, 也就是下文“雖體解吾猶未變兮”所言的 “體解”,是將肢體分裂的一種酷刑。楚屈原已多次地向讀者透露他的寧死不屈或慷慨赴死的計劃,這當然是編輯者們的計劃。
為自己心中美好的理想不但奮鬥終生,而且九死不悔,這是很動人的人格。然則爲了那根本不能實現的理想爲所欲爲,不但荒謬地粉飾美化其理想,而且將一切與自己的理想相左的思想、主張一概斥之爲奸佞或異端,此等人不得志則成爲孤獨者,得志則最可能成爲專制者。爲了美化那莫須有的屈原,編輯者實在費盡了心機;爲了保護另一也被掩蓋在屈原名下“不世出” 的蓋世英雄,王逸們又不得不大肆放手美化屈原。真是好戲啊。
我們應弄清楚,屈原為之“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心之所善”畢竟是什麽?是美政嗎? 是什麽美政?如何實現?實現過嗎?其前其後實現過嗎?
第七段 溘死流亡 蛾眉失意
怨靈修之浩蕩兮(上政迷亂則下怨,父行悖惑則子恨。靈修,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云“子之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傲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眾女嫉余之蛾眉兮(眾女謂眾臣也,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故以喻臣也。蛾眉,好貌),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猶譖也。淫,邪也。言眾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眾臣嫉妒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競周容以為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忳鬱邑余侘傺兮(忳,憂貌。侘傺,失誌貌。侘,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々而憂,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誌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余不忍為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為邪淫之態)。
段意:眾女妒己之蛾眉而謗之于君,導致枉法亂政,自己則受困失志, 寧死不從惡俗。--此忠臣悲劇又一版本,而爲假屈原造勢耳。簡言之,秉持芳德反成被誣之由,哀嘆民生多艱,不惜爲之一死。
作者:真屈原劉正則不可能如此低首下心自譬蛾眉。其父劉安顫顫巍巍小心事君倒有可能。觀其預示投水,應是編輯之設。所以此段應是被編輯過的“淮南資料庫”文字。
要點:蛾眉 規矩繩墨 溘死流亡
32 蛾眉論
“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自譬蛾眉而傲世疾時,其實不能擺脫奴婢心態;是爲此言者所以遭受讒害,以致窮途也。然此話非劉正則所能言,編輯者有意使 “楚屈原”作忠奴之言也。王逸注“眾女謂眾臣也”、“女,陰也”(臣亦陰也),無專擅之義”,其意思是女子求寵則可,卻不可擅寵;男子冷落自己而移寵他愛,女子也應迎合其意,不但接受,而且悅從。同理也適用于臣,故 “猶君動而臣隨也”,即像君王一有所動,臣立刻就跟上去迎合一樣,“故以喻臣也”。“蛾眉,好貌”(蛾眉,即美麗的樣子、大概也是暴君認定的忠誠的樣子)。“眾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眾臣嫉妒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王注明白顯示了眾女與眾臣的相似地位。蓋 “女無美惡, 入室見嫉;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作爲妾或臣,一室之婦與一朝之臣一樣,他們不得不互相防備、嫉妒、鬥爭,都在壓抑人性的同質而不合理制度基礎上、限制下,保護和發展自己事主從政的地位、利益。所以蛾眉事夫猶忠臣事君,只能 “履欃槍以為綦”,而“蹈惡人足跡”,走在低下卑惡之路上,而且動輒受譖毀,或者譖毀別人。
揚雄《反離騷》原文及注解正表明這一點:“帶鈎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應劭曰“鈎,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欃槍,妖星也。”晋灼曰“綦,履跡也。此反屈原雖佩帶方平之行,而蹈惡人足跡,以致放退也”(見《漢書·楊雄傳》)。晉灼解釋楊雄“反屈原”之意,乃說屈原雖中規中矩、佩方帶平,卻走在惡人的足跡上,才導致被流放和斥退;晉灼當然不能如我們今天一樣説透,但他的用意很清楚:自譬蛾眉, 就把自己和眾女放在向暴君昏君爭寵的同等地位,自然“蹈惡人足跡”了。他把一夫多妻制下的眾女, 比之於獨夫暴君下的眾臣,這時“蛾眉”再美、“忠臣”再忠,人格上已被迫沉淪,臣即僕、女即奴,已失去平等、獨立之人格,女子要順夫君意,臣子要順君主意,即使是暴君,仍然要順,順其意還不足,還要與惡黨同伴比賽忠誠度乃至諂媚的本領!以揚其蛾眉邀昏君之寵,就必然墮入受眾女奴嫉妒、謠諑的怪圈,這時自衛則與對方陷入同類之惡,不自衛則任人誣蔑亦終成惡者。如此忠臣,最幸運者受夠冤屈後,或可被昏君平反而略示其“英明”的憐憫,已是天恩浩蕩和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其實,所謂忠臣與奸臣簡直是君王左右手, 取悅其君的時間和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又《反離騷》以下二句“知眾嫮之嫉妒兮,何必揚累之蛾眉”—本來就是對自譬蛾眉的質疑:既然早就明白眾女嫉妒,你這位“湘累” 何必揚起蛾眉和她們爭寵呢·?洪興祖《補注》評此曰 “此亦班孟堅、顔之推以為“露才揚己”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 “不由其道”者,而以污原,何哉”?洪以爲:過度修飾自己的容顔就會引人起淫邪之心、由眼神挑逗接上以心相許,是《孟子》説的“通過不合道義的途徑得到” ,竟用這種方式污蔑屈原,這算什麽道理呢?洪對《楚辭》中顯現的屈原形象持絕對贊揚、不容任何批評的態度,在此毫無道理地批評班固和顔之推,應因他未讀懂王逸、太銳意于以補注《楚辭》向宋皇表忠,其心可憫可鄙也。
錢鍾書論則引《招魂》“二八侍列”云云,謂屈原者果然“善淫”。這是另一題目。我們將在下文討論屈原求女時涉及,真屈原通過“房中之術”求仙的實踐活動,包含追求和交接從嬪妃到下女的各個層次的女性,當時諸侯王如願意,皆能如此,不足爲怪,也不足為罪,所以説他善淫,并不冤枉,也不足為其褒貶。
33 規矩繩墨
王注“偭規矩而改錯” 說百工“背違先聖之法”,或 “背去規矩,更造方圓”;注“背繩墨以追曲”, “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 等等, 都是説人臣背去規矩或背棄忠直之意。規矩是聖賢老祖宗留下的老規矩, 必須恪守,當然不可另造方圓而危君國。至於繩墨,則可代表忠直之道,也必須行之踐之, 否則便容易“隨從枉佞、而被刑戮“。考慮到所謂“楚國”之危亂,終被刑戮者不是那些“隨從枉佞”者流,竟然是行忠直之道的真屈原劉正則及其隨從者,還是感到了此處對於“規矩”和“繩墨”表面的贊頌中暗含的反諷之意。
34 溘死流亡
“寧溘死以流亡兮”(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 ,王注意思是我寧可忽然死掉,身體隨水流去找不到,這其實就是將要選擇投水而死的另一表達。 《九歌·惜往日》 亦有此句(一字之差),“寧溘死而流亡兮”(意欲淹没,隨水去也),是想淹死自己,然後隨水流而去,意思與《離騷》本句差不多。又《九歌·悲回風》“ 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常愁” 王注“意欲終命,心乃快也。逝,一作溘”—也是類似意思。總之,三句語義略同。我們順便說,在整部《楚辭》中,加上多次提到效法或者向往彭咸的例句,共二十多次吧。每次都發自所謂“屈原”,都是編輯者安排他屢次發此哀聲的。決志要死者,有必要重言其事如此多次嗎?這難道還能説不是編輯統一籌劃、改動的結果嗎?虛幻造假而生出的屈原,就算讓他投水一百次,他也不會變成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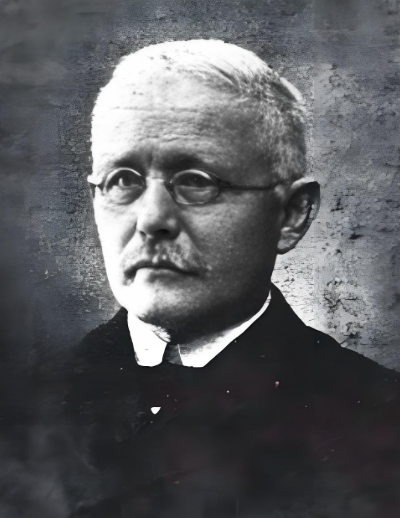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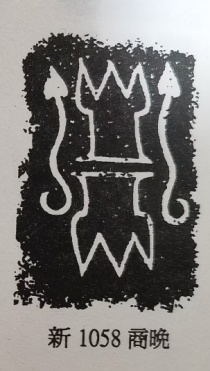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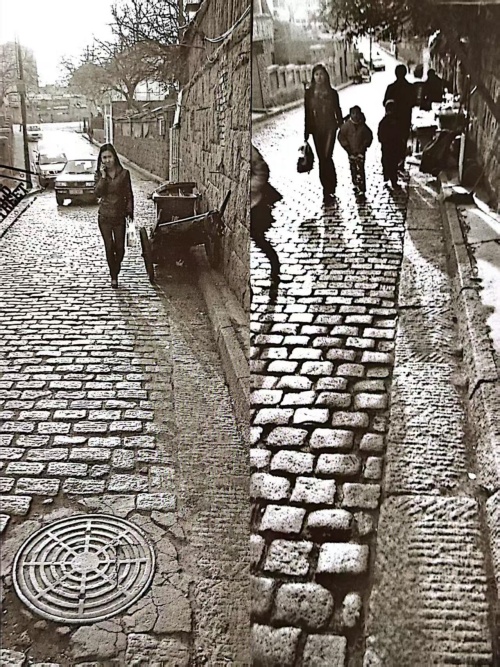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