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三十五岁
我侍奉父母住在北京。当时财政总长是周自齐,派我到财政部总务厅担任佥事上行走。那时郝鹏任该厅文书科长,沈恒祺任会计科长,都是我的旧相识,所以这段日子过得颇为安适。
袁世凯(项城)正准备变更国体,实行帝制,筹备洪宪大典。因为先父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被聘为总统府顾问,与王聘卿(王士珍)等人并称“香山四友”。但先父患有心脏漏血症,哮喘得很厉害。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三十六岁
财政部派我担任公估局局长。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三十七岁
先父病情更加严重,请了西医来诊治也没有用,最终在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三至五时(申时)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那时,蔡锷(松坡)已通电反对帝制,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去世后,道路不通畅,无法将灵柩运回杭州安葬。先父在临终前几天,曾说过想回济南安葬。济南东关外的姚家庄,原来有几百地,姚诗岑曾说那里是上好的坟地。于是在民国五年(1916年)九月,我们将先父卜葬于该地。
我从此失去了父亲。父亲的深恩厚德,我终生难以报答。每每追念他的养育教诲之恩,深感自己能回报的万不及一。只有更加努力地修身反省,期望不致败坏家门声誉而已。
附赵小鲁世丈挽诗(现代白话文参考译文)
(题目:春日哭朱大蜕尘)
春天为何如此匆匆?春日的阴云为何如此昏暗?岁月苦苦相逼,竟与人的寿命相争。造化为何如此不仁,夺走了我坚贞的友人?噩耗突然传来,我痛哭失声。
我与您初次订交时,我才十七岁。惭愧我比您年长一岁,但事事都不及您的才能。您的学问渊博通透,经史子集纵横贯通。为何不让您去著述,在朝廷担任要职?您喜好读书,平时手不释卷,著有《南史节钞》等书。您的志向高远宏大,有整顿天下、澄清宇内的抱负。为何不让您出任宰相,辅佐教化、明正刑赏?您有做官的才干,政绩遍及山东(周齐青之地)。为何不让您担当封疆大吏,成为国家的栋梁?您有识人之明,贤能愚劣都逃不过您的眼睛。为何不让您主管选拔官员,像持秤一样衡量人才?您有应对外交的方略,中外知名。为何不让您主持外交,在谈笑间化解干戈?(提及山东条约之事,后任官员知其内情,委派您驳斥修改,众人都认为不能改变,您据理力争,德国人最终屈服改约。)
您一生清高傲岸,昂首挺胸,不肯屈就。既然遇不到真正的赏识,纵有翅膀也难以高飞。人事已阻碍了您的际遇,上天又缩短了您的生命。可惜啊,您的抱负未能施展,这颗心怎能瞑目?
我与您交情深厚,历时愈久情谊愈坚。我与您缘分不浅,踪迹时常相随。从求学直到出仕,我们未曾分离。您知道我粗疏旷达,为我谋划思虑周全。您知道我愚钝糊涂,时常提点使我清醒。经济上的接济更是小事,常让我住在您家。相交五十年,情谊如同亲兄弟。为何您静极思动,决然前往北京?听您说起意图,我半夜里心绪不宁。见您准备车马,我热泪盈眶。您问我为何如此,我说不清缘由,只觉得这次出行不祥,让我心中不安。哪料到竟成永别,从此阴阳两隔。
去年我探望您的病情,那时病还未深入膏肓。我深深懊悔匆匆东归,以致未能见您最后一面。虽然留下也无力回天,但我的愧疚或可稍轻。从此我废弃医道,不再阅读《灵枢》《素问》。
您家有贤德的夫人,持家严谨,恪守前规。您家有出色的儿子,能继承您的事业,守成家声。您况且著作丰富,更留身后之名。您固然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却感到孤苦伶仃。黄泉之下若有好的居所,请为我留几间房。我也不会久留于人世,将来会去寻您,同游泉下。您死了有我为您写悼文,我死了又有谁为我写墓志铭呢?屋檐外冷风凄凄,桌案上灯火荧荧。哀哉,您的魂魄归来吧,让我再看看您的音容笑貌。
又吴鹗《朱司使家传》(现代白话文参考译文)
仁和县的朱公,名钟琪,字养田,晚年号蜕庐。幼年随父亲筠舫先生在费县、滕县的官署中生活,熟悉官场事务。筠舫先生勤于政事,家中事务和生产都交给朱公管理,无不处理得当,父亲非常赞许他的能干。
朱公喜好读书,每天必定读完数卷,从早到晚,无论寒暑从不间断。即使宾客文书堆在面前,也不停止阅读,手抄的笔记积满了箱箧。尤其精通南史北史,同时擅长书法。他为人慷慨激昂,如同古代的壮士,但书法却工整秀丽,宛如女子所写。他立身处世尤其光明磊落,不因个人嗜好而受拖累,与世上那些徒然仰慕道学的人不同。
朱公起初以文学进取,但多次科举考试不中,这才尝试做小吏。后捐资以知县身份到山东候补。刚到省城,就奉命代理寿张县知县。寿张向来是盗匪聚集之地,朱公到任后擒获惩治了匪首(所谓“大大王”、“二大王”),境内得以安宁,邻县的盗匪也不敢来犯。任期满了离任,济宁知州立即发文书让他代理嘉祥县知县。嘉祥县是山东最贫困凋敝的地方,老练的官吏都不愿去。朱公任职仅三个月,就颂声大作,他自己却因时间太短未能完全施展抱负而感到遗憾。不久,他进入福建巡抚幕府参与机要,积累资历后补授招远县知县。招远地方贫瘠,但山水秀美,风俗鄙陋,文教不兴。朱公延请饱学儒士丁咸亭、陈用民两位先生讲学,又选择特别优秀的士子,亲自教授,当地文风为之一变。
过了一年调任兰山县知县。前任因事去职,留下巨额亏空,朱公挺身承担,时人认为他有侠义之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兰山县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军队北上京师、东防海港,都经过兰山。兰山北到泰安、东到诸城,都近四百里。军队行进急需车马,有时找不到,就强抓民间车辆,往往有去无回。朱公设立车马局,预先准备数千车马等候,又与其他县约定照此办法办理。军队通行无阻,百姓也称便。但官府的亏空因此更加严重。后来李秉衡(谥忠节)巡抚山东,听信流言,将朱公调回招远。朱公于是上书李公陈述时事,李公转而重视他的才能,疑虑也全部消除。调他升任清平知县。到任后修缮城郭,整治盗贼,政事平和,诉讼得理,治理得从容不迫。清平有巨匪卢池,已接受招安,担任临清等地民团队长,但其党羽仍在暗中劫掠。李公催捕甚急,临清知州无法治理,东昌知府也不负责任。朱公独自定计,准备缉拿盗匪,嘱咐卢池将他们招来,假意设宴,酒宴中伏兵突起,擒获卢池及其党羽五人,解送省城法办。地方上感激朱公,同僚中有人以怕报复为由为他担忧,朱公不居功,也不自知其中危险。李公更加认为他有才干,调他任单县知县。刚三个月,又调任历城知县。单县多盗,他像在寿张时一样治理,并与参将岳某联合,盗匪因此收敛。历城是首县,事务繁重困难,别人当这个官整天忙不过来,朱公却趁此机会,用经学儒术来整治风俗。戊戌政变后,他知道科举八股不足为学,在官署设立“泽古文社”,召集优秀生员,用经史引导他们,以策论考核。我的儿子(吴)曜、侄子(朱)是,都曾在那里就学。一时当地人文振兴,后来那些倡言维新甚至奔走国事的人,很多出自文社。那年李鸿章(文忠)巡视河工来到山东,溥贝子(载振)为查办某案随后也到。两位钦差同时驻节,且都是勋贵,事务之繁杂,供应之劳累,应付之困难,听闻者和见到者都头疼皱眉,而朱公却处理得从容自如。豪仆骄兵,有时加以抑制也不敢违抗,因为他理直而内心无所畏惧,气平而外在无所屈服。次年调任泰安知县。他仰慕石徂徕的遗风,在泰山脚下建仰德书院,用泽古文社的规矩课试士子,成才的也很多。又在白鹤泉边建思鹤堂,召集宾客在其中吟咏唱和,世人比作欧阳修的平山堂。
胶澳条约签订后,来泰安的德国人很多,而且骄横,常逾越常规。有个叫费某的德国人,在泰山下因一句小事,将当地人李大全殴打致死。朱公听闻后非常愤慨,详细勘查后上报,并坚决请求辞官,带着死者家属赴青岛起诉。德国人已准备认罪了,恰逢义和团事起,袁世凯巡抚山东,将朱公召回。五天内三次升迁,以知府身份任东路军巡防营务处,代理青州知府。他与袁公一心整治匪患,动用重典,能在奸邪未发时洞察,在祸患初起时消除。练兵筹饷,山东以东以青州为重镇。次年解职,归入道员班次。袁公因匪乱未平,更急于筹措饷银,并重视商业,采取治标治本之计,特设筹款局、商务局,均奏请朱公和唐绍仪总理其事。袁公带唐绍仪赴北洋后,继任的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又倚重朱公如左右手。朱公也越发施展才干,任职七年,筹款使每年收入增加八十万两白银。商务方面,扶持官银号于将倒之时,在既成事实下争回五矿权,在全省设立商务总会。此外,还设立东阜公司以利运输,设工艺局以惠及工匠,设商埠局以通商,设农桑试验场以重视农业。并创立公立学堂、山东官书局、济南报馆。即便是官立的高等学堂、客籍学堂,也由朱公建议而次第设立。辛丑条约后,清廷开始提议推行新政,但这些举措无不起始于山东省,无一不是朱公所倡导。谈论时务的人于是以山东为模范。
朱公的名声既已显著,嫉妒诽谤也随之而来。恰逢钦差大臣来查办杨士骧,杨公便弹劾朱公及曹州知府丁镗以求解脱,其实都并非他们的罪过。朱公去职后,神态自若,如同平时。山东有人愤愤不平。张之洞(南皮人)、赵尔巽(襄平人)先后调朱公至湖北担任总文案。过了一年,特奏请朝廷予以开复(恢复原官衔)。赵尔巽总督东三省时,还奏请朱公担任度支使、民政使。在湖北、在奉天,时间都不长,未能充分施展抱负,但他的意志风采,一如在山东时。
壬子年(1912年)国体改革,朱公浩然归去,在青岛定居,闭门读书,不再过问世事。袁公就任大总统后,屡次征询政见,因此有时也到北京走走,但做官的心思已淡如止水。议论者认为,民国初年的政治,若有几位像朱公这样的人出来辅佐,其成效或许可观,应当不至于出现喧嚣强横、急功近利、贪图权位利益而被世人诟病的情况。但这又岂是朱公的志向所在?世人都为朱公的才能未能尽用而可惜,却不知朱公的节操未曾稍屈更为可贵。民国十年(1921年),世道日益混乱,风俗日益败坏,道德沦丧,名节败坏,越来越严重。朱公幸而早逝,不然的话,他该会如何地痛哭长叹啊!
朱公于丙辰年(1916年)三月在北京寓所去世,归葬于济南,送葬的人堵塞了道路,他感人之深竟到如此地步,也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夫人是华亭袁氏,有才干韬略,尤其能以勤俭辅助朱公。妾邹氏、言氏先于朱公去世。妾张氏在朱公灵前服毒殉节,被救活后,进入教会坚守其志。儿子二人,长子朱曜,曾任知府、财政部公估局局长、官硝厂厂长;次子朱晟,在财政部任佥事上行走。女儿二人,长女嫁叶景葵,次女嫁王传经。朱公去世时六十四岁,所著《南史节钞》藏于家中。
吴鹗评论说:朱公以知人善任闻名,所办理的事务多属创举,而其才能仿佛天生具备。他能根据别人的长处来任用,既教诲又劝诫,使之人不跌倒也不懈怠。上级官府如果需要人才,向朱公咨询征取,无不得到满意人选,或者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当时的舆论很推重他。他幕府中的宾客李黯、李熙,尤其是天下奇才,可惜他们默默无闻而终。如今只有袁大启、叶景葵,在银行业干得出色。我(吴鹗)从政时间久,各种事件没有不参与的,深知朱公内心的隐痛,他的志向很少能假手他人而告成。如今我也老了,无法报答朱公的知遇之恩,真是惭愧啊!惭愧啊!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三十八岁
张勋复辟事变发生。因为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黄陂)继任大总统。黎虽是汉口革命元勋,但兵权多属袁世凯北洋旧部,不太服从他,总统府与国务院也不能合作,议会更是多有掣肘。张勋坐镇徐州,一向宣称效忠清廷,部队留着辫子。此时他乘机而动,带兵进入北京,直接挂起龙旗,宣布恢复清廷。但他所联络的军人,并非都支持他。段祺瑞(合肥)于是从天津赶到马厂誓师,偕同其师长李长泰,宣布张勋罪状进行讨伐。段祺瑞派段芝贵(香岩)为讨逆军总司令,派冯玉祥疾驰至廊坊,接收其旧部第十六混成旅(原文误作十七旅)。安徽督军倪嗣冲等人响应。而保定的曹锟督军,张勋曾事先派人接洽,此时也表示与讨逆军合作。
我因为先父曾担任过袁世凯武卫右军的执法营务处官员,所以与段芝贵公是世交,他招我充当他的幕僚。我随即参与了接收天津电话局以保障通讯的工作。半夜得知廊坊接收成功,就立刻赶赴北京。三天后大局已定,张勋复辟失败。冯国璋(河间)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我被授予陆军少将衔。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三十九岁
我纳唐宛宜为侧室。唐宛宜是广东中山县人,王祝三是她的义父,经他介绍而成。我租用了王祝三在北京东拴马桩住宅的西偏院居住。唐宛宜十四岁跟我,十五岁怀孕,我禀明家中后接她回家。她十六岁那年(推算约为1919年)六月十七日生长子传榘。十七岁生次女传雅(字尚柔),后嫁辽阳唐秉初。十九岁生三女传懿,后嫁天津刘绍宸。二十岁生四女传训,后嫁湖州沈蕴昌。二十二岁生次子传一。二十三岁生五女传荣,因揆初姐夫家无子,便寄养在大姑家,取名喈喈,后嫁潮州郭启新。
段祺瑞(合肥)既是参战勋臣,又有讨逆首功,且是北洋宿将,声望日隆。他任用徐树铮为外蒙专使。徐树铮才气纵横,文武双全,但不免稍露骄矜之气。他因陆建章反复欺诈,将其在家中枪杀,因此遭到直系忌恨(陆是冯玉祥的旧长官,故冯尤其恨他)。当时直系以冯国璋(河间)为首,包括直隶督军曹锟、江苏督军李纯及吴佩孚等。皖系以段祺瑞(合肥)为首,包括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卢永祥、山东督军张怀芝及段芝贵、吴光新、曲同丰、徐树铮等。我因参加讨逆之役,故与皖系较为接近。
徐树铮略历(现代白话文参考译文)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徐州萧县人。袁世凯督师山东时,他曾以平民身份上书万言陈述政见。袁世凯命我先父与他接谈,先父很器重他,向袁世凯汇报,资助他学习陆军,交给段祺瑞(合肥)试用,所以他拜段祺瑞为师。他与王祝三交情很深,告诉我我们是世交,他是因为得到我先父的赏识,才有后来的地位。后来我查阅先父日记,里面记载着:“徐州布衣徐树铮,以万言书求见袁世凯,命我接见。此人才气纵横,定当杰出,但须收敛才华,归于规范,否则恐怕容易招致灾祸。”我把日记给徐树铮看,他也深表敬佩。
徐树铮酒量极好,擅长唱昆曲,文章颇为精深。我的舍弟朱是(去非)曾担任他的秘书,也有文名。但有时批拟公文偶有不妥,徐树铮修改后,仍会详细批注其来龙去脉,常常长达数千字。他曾教授曾毓隽(云霈)的女儿和我的夫人读《孟子》,讲解得清晰透彻。他出使外蒙古时,很能运用怀柔策略,深有成效。
直皖战争时,皖系失败。徐树铮蜷缩在柳条筐里,逃到天津,后远游欧美。等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他回国,从天津乘火车去北京,行至廊坊时,被冯玉祥派部下拉下车枪杀。先父日记中的话果然应验了,所以一并记录下来。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四十岁,至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四十二岁
我担任财政部直属的直鲁豫京兆四省官硝厂厂长。官硝厂的设立,是基于盐政统一的考虑。因为硝石是制造火药的原料,产于乡村的墙根屋角,仲春时节产出,乡民扫取后,用柴火熬炼,沉淀底部的为硝盐,浮在上面的结成硝石。质量好的晶莹剔透如冰柱,称为“凌硝”,可制作鞭炮、火药及硝酸银。硝石原本属军部管辖,与硫磺并称。而硝盐味苦,再经提熬,可充当食盐,腌制肉类颜色发红,味道尤其鲜美。但因私盐冲击官盐销售,妨碍盐政,故将硝盐事务划归盐务署管辖。规定所产硝盐,由官方定价收购,然后挖坑用开水销毁;硝石则由军部领取执照出售。
但此事属于创办阶段,拨款很少,而四省地域辽阔,稽查极为困难。除了京兆、直隶地区尚能服从命令外,山东、河南的分局,都正值督军专权之时,藉口抗命。我经过悉心研究,撰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分析各地的产质、产量、用途及未来计划,可惜这本书在后来的乱事中遗失了。值得记录的是:硝石质量以雄县、霸县出产的最佳,可得百分之八九十的纯硝;直隶其他县次之;京兆又次之;山东再次之,其西部曹州府所属地区更差;河南开封、兰考(原文兰州疑为兰封或兰考之误)产的最劣,纯度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但如果运到总厂再加提熬,也可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销路可售予上海、苏州、杭州的鞭炮业,因为南方不产此物。但销量不大。日本军部曾来采购过两次,由天津驻屯军委托大仓洋行(原文火仓洋行)代办。签约后,经其技师化验,双方各保存样本。第一次用的是雄、霸产的硝和总局加提的硝,对方没有异议。第二次,正好山西方面派人托售烤硝,因总局库存不多,就把山西硝卖给了他们。经其技师化验,也称合用。但运到日本后,对方却说硝质太劣,派参谋金井来交涉。我笑着回答:“我方用的是土法熬炼,不懂成分。技师是贵方所派,亲自抽样验收,只能由技师负责。”他无话可说地走了。后来大仓洋行的人来说,他们这里的化验方法是没有“白银锅”的,提验法是先提炼出硝石,剩下的是硝盐,所以提得不净;而东京兵工厂的化验法是先去除硝盐,剩下的是硝石,所以成分较纯。我当然不再深究。实际上,是所供硝石的产地不同导致的。
对于规定要销毁硝盐,我认为很不合理。化无用为有用,是古有明训。现在将有用的东西,花钱收购,再费工销毁,似乎不明智。而且埋在土里,是否可能被人重新挖出熬炼,流弊很多。于是我找了一位叫叶瑾仲的技师研究,他说硝盐也可用来制造漂白粉和硫化碱等。我便自己出资,托他去日本聘请技师、购买机器、建造工厂。我们凿井修池,用碳素板建造了三间贮气室。计划先将硝盐气化,通过铁管输入贮气室,再经石灰调匀,制成漂白粉。没想到彻底失败了。原因有三:一、含硝的盐腐蚀性很强,导致碳素板极易损坏,铁管也易破漏。二、硝盐气化时,硝轻盐重,硝先蒸发,盐后蒸发,遇冷后,硝气先凝结,堵塞管道,盐气无法通过。三、贮气室内的气体,没有机械搅拌,下层石灰接触不到气体;若用人进去搅拌,氯气又让人难以忍受;若在室外用木耙拉扯搅拌,则搅拌孔又会漏气。所以办了一年多,赔累不堪,只好停业。我私有的中兴煤矿公司股票也赔了进去。这实在是由于知识不足,匆忙试办工业的过错。
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四十三岁
先母七十正寿,在天津祝寿。从济南来的宾客有孙念希、沈景臣、邹心一等人。孙念希介绍他的表弟马骥良与我的女儿(朱)传棠联姻。我便先推荐马骥良到华北银行练习,以便观察他。华北银行是我和郝鹏(字雨苍)、李思浩(字赞侯)等人组织的,任命章晴孙为经理。郝鹏是我在山东的旧交。李思浩在民国初年于财政部盐务署任佥事,为人极其诚恳忠厚,精通公文,办事勤勉廉洁谨慎,是我知交中最可信赖的持久朋友。我晚年多依靠他。
民国十二年(癸亥,1923年),四十四岁
先母患腹内肿瘤,肿瘤日益长大,肿痛。医生说是恶性瘤的可能性大,屡经医治无效,我非常忧虑。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四十五岁
张弧(字岱杉)任财政总长。当时吴佩孚势力很大,钟世铭任盐务署长,与张总长不太融洽。于是,(张弧)将官硝厂委派给了钟世铭的人。我辞去官职,担任了中兴煤矿公司的常务董事兼营业主任。
民国十四年(乙丑,1925年),四十六岁
长女传诗出嫁,嫁给绍兴马骥良。马骥良在华北银行服务颇为勤勉谨慎。这时他的兄长马贯之来主婚,孙念希、王子香做大宾。婚礼在国民饭店举行,宾客极一时之盛。但马家家境清寒,由孙念希垫款一千元承办。我除了置办妆奁,另外赠予他们六千元。
张弧再次出任财政总长,钱方轼任盐务署长,任命我为盐务署总务处处长。张总长很有才干,是袁世凯时代有名的三位次长之一,曾与盐务稽核所总办英国人丁恩订立盐务借款,统一盐政。但他为人豪放,不拘小节,有时也受人蒙蔽。如果有人能把事情原委说清楚,他会毅然更正。钱方轼是钱嵘世伯的第三子,留学英美,极为诚笃,在稽核所多年,丁恩很器重他,但对旧式公文不太熟悉,所以命我主持总务处。凡是场产、运销两厅的事务,也让我参与以备咨询。
曾有三件案子批下来要求盐务署照办:
(一)青岛日本归还的盐田,招商投标承办事。因第一中标人自动放弃,第二中标人是山东东纲盐商张竹铭,第三是青岛商人丁敬臣,第四是青岛商人隋石卿。丁敬臣是江苏人,在青岛经商,不懂盐务,为人颇刁滑,他与久大精盐公司的景本白(景学钤)联合,景本白代为接洽稽核总所丁恩,丁恩同意由丁敬臣接办。但这些盐田在山东,按理由东纲盐商承办最合适。但张竹铭懦弱,丁敬臣恐吓他,使他不敢接受。隋石卿在青岛没来接洽。所以只得给了丁氏,但要求他与东纲合作。于是丁、张、景联合成立了永裕公司。后来丁敬臣回青岛,隋石卿唆使盐户殴打他,几乎毙命。
(二)吉黑榷运局报销事。当时奉系张作霖入关,声势很大。吉黑榷运局长阎廷瑞是张作霖信任的人,大中银行孙仲山代为说项,要求批准其报销。张总长已经同意批准,但其中多有不合手续之处,我不肯副署。张总长打电话责备我,说他是总长,责任由他负,我为何阻挠。我便当面陈述原委,张总长立即改了批示。
(三)北京女子商业银行募股事。该银行是陈香元创办,盐务署曾答应入股但未交款。这时陈香元呈文部里,请张总长批示照付。但该行亏损已停办,账册已送到警厅,此时付款必遭非议。所以我驳回了,不予支付。
后来王克敏代理财政部,告诉我有人要对张弧不利。张弧乘汽车避往天津,而查办命令下达。接替我盐务署总务处长位置的徐某和参事李律阁奉命检查案卷,想找些问题弹劾。就查了上述三案,但因查不出弊病而作罢。李律阁当面告诉我:“你是个好小子。”张弧后来对人说,公文交给朱某核办后,不看也可以签发,决不会有差错。
四弟去非(朱是,字去非)因肋膜炎在天津去世。自从先父母护送祖父母灵柩回杭州,安葬于丁髻峰后,(我们一家)就与堂叔燮臣公一起来到济宁同居。燮叔奉侍我的叔祖母和婶母沈氏,带着去非弟同来。弟弟原名祥晖,因为祖母钟爱,有些骄纵,惹人厌烦。第二年婶母因肺病去世,继母孙氏对他不加怜爱。于是他发奋读书,改名朱是,字去非,别号硁斋,与我同窗共读。他非常聪颖,远超过我,擅长诗词,能作骈体文。性格耿直,不徇私情,嫉恶如仇。但戆直不合时宜,郁郁不得志。后来被徐树铮(又铮)赏识,在外蒙古充任秘书,很受信任。直皖战争后,徐树铮失败寓居天津。等到徐树铮遇害,弟弟大哭得病,竟至一病不起。知己朋友都感到痛惜。他生有二子,长子早夭,次子宪武;有二女。
我曾写祭文痛陈往事,附录如下:
时维中华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某月某日,身着丧服的兄长朱曜,恭敬地备下清酒与各样祭品,致祭于亡弟去非的灵前,泣告道:
唉!去非,你就这样真的去世了吗?
难道是因为众人都浑浊而你独清?众人都沉醉而你独醒吗?为何你怀着澄清天下的志向,反倒因此缩短了自己的生命?为何你肩负着启迪后辈的责任,却未能看到他们成长有成?为何你如此看重兄弟情义,竟最终舍我而去?是时运不等人、命数当尽吗?抑或是世风日下,连你这般被压抑的磊落正直、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也不容许在世间宣泄不平吗?唉,悲哀啊!
回想弟弟你四岁时,才来到任城(今济宁)。刚开始学习基础知识,就已经懂得尊敬兄长。第二年不幸丧母,由祖母抚养。祖母对你爱护怜惜,使你带着些骄矜之气长大。祖母去世后,你失去了庇护,与继母关系不睦,于是放纵饮酒,沉溺玩乐,行为渐渐不拘约束。
到了十六岁,你到济南求学。当时我父亲(你伯父)是当地文坛领袖,常有诗坛文社的聚会,“泽古社”的各位先生中,以吴、李二位尤为杰出。你与他们切磋学问,于是也跻身于当时的名士之流。
弟弟你立身处世,以刚直不阿自誓。你侍奉主君(指徐树铮),始终如一。然而,刚直则易受挫折,为邪曲之辈所不容;执着如一则难以与世俗苟合,最终导致困顿潦倒。虽然气节得以保全,但功名事业终究受阻。命运与自身相悖,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结局。
起初你治理恩县,政绩堪称最好。但代理期届满,接任者迟迟未到,局势突然因盗匪而败坏。后来你追随徐公(徐树铮)做事,徐公倚你如同臂膀。但徐公自身遭遇困顿,你也只好更加收敛锋芒,隐居避祸。
你以廉洁标准约束自己,以至于生活艰难。你以坚贞节操激励世俗,因而朋友稀少。抑郁苦闷,无处倾泻,只能将情感寄托于诗文,但这已是次要的宣泄了。唉,悲哀啊!
性情至真至纯的人,最怕遇到伤感之事。何况弟弟你所经历的,都是深痛巨创:心怀爱国,国家却陷入混乱;尽力事主,主君却遭害身亡;经营财务,财政却匮乏难支;教诲儿子,儿子却早年夭折。今年元旦,你为徐公遇害痛哭,同时又哀悼亡子,百般感触齐聚心头。你决意离世,恐怕是下了决心的吧。弥留之际,你只是沉沉地一笑。
上天不保佑善人,我又能说什么呢?抚摸着你的棺木,我放声痛哭,涕泪交流。你留下的子女,由我这活着的人来负责照料。你的魂魄若有灵,请来享用一杯酒吧!唉,悲哀啊!请来享用吧!
曹锟因贿选受到各方攻击,吴佩孚又与冯玉祥积不相容。奉天督军张作霖联合段祺瑞、冯玉祥合力讨伐曹锟。吴佩孚兵败出走。于是由段祺瑞(合肥)出任临时执政,李思浩(赞侯)任财政总长,张训钦任次长,我充任财政部总务厅厅长。当时冯玉祥、张作霖都因有功驻扎北京,不断索要军饷,极难应付,多派我去支应。
这时发生了“金佛郎案”。查“金佛郎”指的是庚子赔款中法国的部分,是用金佛郎支付还是用纸佛郎支付,差额很大。用金佛郎支付则国库损失大,用纸佛郎则受外交挟制,相关的国际款项支付都会停顿。段祺瑞命李总长解决此案。当时张训钦次长也不明真相,密嘱我向李总长询问原委,说这件事必定会招致非议,除非对国家有大利益,或者对私人大有好处,否则都以不办为妥。我于是在夜间无人时,亲往谒见询问。李总长当即上楼取来公事皮箱,出示段执政的批示,里面有几句大意是:“查外蒙事件,就因为稍有迟疑,以致坐失良机。赞侯(李思浩字)还未明白此意。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应当断然办理,不要顾虑。”才知道办理此案的决心完全出于段执政,并且是出于爱国,绝非卖国。于是告知张次长,共同进行。
当时各省督军专权,山东督军张宗昌扣留盐税,就命我去交涉。我向他陈明利害,张宗昌勉强表示顺从,并邀请我担任山东财政厅长,我婉言谢绝了。所以有关山东的事务,李财长都交给我办理,双方感情处得不错。金佛郎案拟议解决后,德国赔款、奥地利赔款等事也相继办理,外交关系日渐融洽。于是准备发行公债,外交方面也表示承认和赞助。当时李总长对于吴光新在上海协助浙督卢永祥所用的军费,以及张作霖、冯玉祥的索饷,在无法应付时,常常用私人借贷来垫付,打算在公债发行后呈请报销。但事情还没办成,变乱又起。
郭松龄原是奉军将领,与张学良关系密切,这时受到冯玉祥的策动,从山海关回师攻打奉天。李景林时任直隶督军,也属奉系,但张作霖对他遇事责难,此时李景林便联合郭松龄,扣留了奉方将领。而冯玉祥表面与李景林联合,又密派张之江率兵进驻杨村。等到郭松龄兵败,冯玉祥又唆使学生在天坛集合游行,手持红旗,向执政府攻击,并烧抢了曾毓隽(云霈)和李思浩的住宅。曾毓隽被禁锢,李思浩避居东交民巷道胜银行沈吉甫的楼上。我直接去谒见他,告诉他赤化祸乱将起,我打算去天津联络李景林、张宗昌两位督军共同讨赤,李思浩表示赞同。我便先到冯玉祥的军需处长魏某家坐谈,等到下午四点京奉火车快开时,才赶到车站攀上车。到天津后,立即到潘复(字馨航)家告知此意。潘复是张宗昌的顾问,很赞成。当时直隶财政厅长郝鹏、长芦盐务局长张小岱都在座。于是在晚上一同到河北督署谒见李景林。刚开始交谈时,李景林不以为然,说事前李总长既无表示,事后段执政也未到天津共策患难,现在还有什么用。潘复见势将决裂,又知道李景林与郭松龄的关系,便借故溜走了。当时已过夜里十二点,李景林邀我吃夜餐。饭后,我私下对李的警察厅长岳屹说,我想直言责备李督军,如果李督发怒,希望他能设法营救,岳屹答应了。我便直接向李景林陈述利害,指出冯玉祥决容不下他,可以从其进兵杨村得到证明。张宗昌督军有青岛可退,李总长已有安全住所,而您若失败,将无处容身。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与山东联合,声言讨赤,既可得到外交和人民的同情,也可得到张作霖的谅解,即使失败也有地方可退。李景林这才恍然大悟,说他连夜思考,没找到好办法,现在决心已定,就连夜发出了讨赤通电,与冯军开战。起初打胜了,再战却失败了,只得乘船逃走,经青岛到了济南。我也追随前往。张宗昌命我去奉天为李景林疏通解释。等我回到山东后,正值苏浙皖三省联帅孙传芳,命靳云鹗进攻山东,进驻兖州。张宗昌又命我去兖州游说靳云鹗罢兵。靳云鹗答应了,交还了火车一千辆。
我于是就去就任德韩铁路局局长(因津浦路北段只通到德州,南段只通到韩庄,故称德韩铁路)。当即在济南旧工程处大楼成立路局,局员全用旧部下,任命苏步滨段长兼车务处长,所以事情容易开展。(待续)
编后:原文是文白混杂,为便于阅读,现改为现代白话文
原文请见 沈保立丨我的外公朱熙齡回忆录(朱旭初自传·之三)
沈保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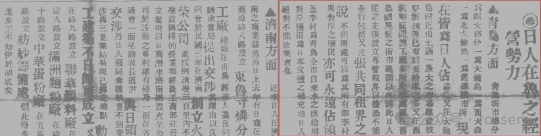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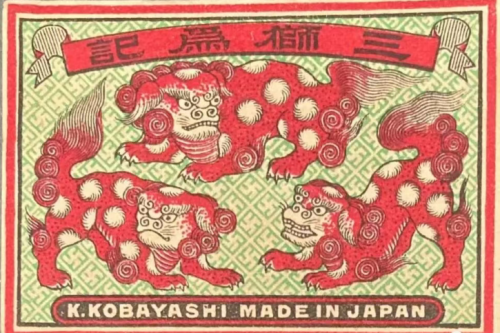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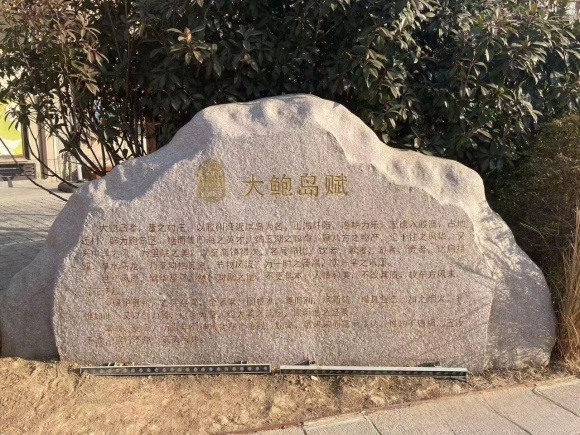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