阽余身而危死兮(阽dian4,猶危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己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伏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固前脩以葅醢(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葅醢,龍逢、梅伯是也)。曾歔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欷,懼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葅醢之日)。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軟也。沾余襟之浪浪(沾,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沾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軟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跪敷衽以陳詞兮(敷,布也),耿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睹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第十五段),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見第十四段),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葅醢(第十四段與本段)。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情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
段意:自己用義服善,危死不悔;哀嘆朕時不當,卻因悲而悟中正之道也。
作者:劉正則,但摻有編輯者對假屈原的暗諷。
要點:前修葅醢 朕時不當 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 得此中正
44 前修葅醢
第十三段B已言“后辛之葅醢(梅伯)兮”,今又舉夏之關龍逢、商之梅伯二位前修之遇君無德而被葅醢,説自己雖事昏暴之君,卻不肯量鑿正枘,即不能考慮君之賢愚而定服侍他的方式;自己不悔其初之堅持正言危行,等於明説要效法前修而求死,明知求死無益仍要求死。不避其死,而死自至矣。
45 朕時不當
“朕時不當”,王逸注“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也,其實即“自傷不值於堯”,即未遇聖君如堯舉舜自代一樣來推舉自己。亦言現時非其 “以朕自稱”(稱朕)之時也。“而值葅醢之日” 者,預知慘死無日、慘死有日也。這個朕,指的當然是劉正則。
46 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
王逸這話意思是,不因爲悲傷、放逐,就喪失仁義的原則。對何事這樣講解呢?就是解釋 “攬茹蕙以掩涕兮”二句意蘊時。王注曰“茹,柔軟也。……言自傷放在山澤(此句所陳放在山澤當然如前所析是假的),心悲泣下,沾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軟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原文表達的因放逐而悲傷本來意思很清楚,王注又仔細重復自傷放逐、心悲泣下、沾衣等悲苦字眼,其悲傷自然毋庸置疑;但“引取柔軟香草以自掩拭” ,即用柔軟的蕙草掩面拭淚,畢竟是怎樣解作“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的呢?看來,“引取柔軟香草” 就是引取“仁義之則” ,“柔軟香草” 就代表“仁義之則”。所以,因悲放引取仁義之則,就大致是不因悲放而不引取仁義之則,也就是“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了。王逸在此把僅有一絲可能(因其柔軟?)被比成仁義的 “茹蕙” 當成等於乃至超過仁義道德本身的、幾乎有重量、有形體的實物名曰仁義,簡直如玩魔術一樣造出“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的奇句。 這和前文(第六段)“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之“所持忠信”一樣,屬於編輯者專門為虛無人物之想象的道德而製造出的、名副虛無人物之實的香草仁義之怪癖屬性。“不以悲放失仁義” 中,“悲” 情雖似真,卻全為虛假屈原而生,所以是假的;“以悲放失仁義之則” 因果邏輯雖假,“(錯)失仁義”之道德評價,卻是真的。所以王逸這句話竟是為楚假屈原設計的,更具體地說,是爲描寫假屈原哭的樣子時設計的,卻與前文第五段的“忠信”A遙相呼應而意義貫通,故可稱之爲忠信A之同類,即仁義A也。 這話其實仍暗諷楚假屈原之被放逐,或可説是暗諷被放逐的楚假屈原。
47 得此中正
王注“耿吾既得此中正”説了一大段話。按其意,屈原通過總結歷史,上知聖君修德興天下,下知昏君行惡而亡國,中知前修 “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葅醢”。此處的屈原經過“俯首省念、仰訴於天”(舜很能代表天)的過程,似悟出古今興亡更替中,“執履忠直”如己者必然遭殃、必然敗滅的道理,而達到“中心曉明”的程度,因此終得悟“中正之道”了。什麽是“中正之道”?是天人之道? 還是天仙之道?他是怎樣得道之中、得道之正的?實在都令人感到深不可測。反正“得此中正之道”後,他本來的俗世之情就此升格,而得與真人仙人神人相合相侔;他的神魂便與造化同遊,所以他可以乘雲駕龍、周遊天下了。大概他果真能擺脫聖君、昏君的束縛、也擺脫了“忠臣”、佞臣的羈絆,才能入如此“化境”?王逸為屈原之極天際地的神遊(雲遊)四方,找了一個很神秘的藉口。如此神秘而深沉,其言實為劉正則而發,楚假屈原也跟著沾光而已(他本是很隨和而任人塗抹、濃淡皆宜的)。
第十五段 朝發蒼梧 夕至縣圃
駟玉虯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虯。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鷖,身有五采),溘埃風余上征(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虯,駕鳳車,淹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群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乃維上天。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遍)。
段意:乘龍駕鳳 。至縣圃而留靈瑣 令羲和弭節 上下而求索
作者: 劉安。在劉安與其子劉正則皆為《楚辭》主要作者的前提下,年齡老者就是劉安。 王逸兩次提到他 “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都可解釋成年老之意,這對於原文(日將暮、日車近崦嵫)而言未必是必要的,王偏要强調年老,所以他以此特別指示年齡的意義很明白。故原文作者應指向劉安,或至少是與劉安年齡相若的老者(不是劉安又是何人)。其文應經過編輯者改動、又向楚假屈原有所靠近而已。
要點:設往行遊 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 令羲和弭節 道德不施
48 設往行遊
在以上首二句的注解中,王逸再次提到屈原之乘龍駕鳳、超越塵埃、向上飛行的雲天之遊,這與所謂乘龍駕雲(或乘雲駕龍)是一回事。王注謂屈原“言我設往行遊”,透露這不過是幻想中假設的雲天之遊罷了。哪如上段末句所説得那麽莊重複雜。其實所謂 “言我設往行遊”就是隨興而發,隨思而遊,穿越時間、超越空間,無視邏輯,不顧常識,達到隨心所欲的自由,達到個人精神或其某個側面的無限擴張,不但凌越世俗,而且役使百神,甲瞬間在A,乙瞬間到B,全然不顧時間距離。謂之超越時空。從修行而言,謂之冥想:得其道者,心想而事成; 謂之氣功:得其方者,無羽而飛騰。於是乎入水而仙去,登雲而風行。然而畢竟是碳基之奇絕,不如硅基之凡平。其想象也,多有瞬間之快感,長留遺憾于永恆。其銘感也,堪稱人類之楚歌,生命之悲鳴。前者小而無可奈,後者大而不能平。
49 夕余至乎縣圃
依王逸注,屈原 “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意思是他畢竟還是被舜傳授了大道,才很迅速地從九疑山來到昆侖。《淮南子·地形訓》云 “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凉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此處所引《淮南子》可能正是這位遊昆侖的“屈原”、 即劉正則之作也)。可見,從昆侖之丘向上攀登,翻一倍的高度就到了涼風之山;再翻一倍的高度,就到了縣圃;更翻一倍高度,就到了天帝所居了。每上一倍,道行更深,從肉身凡骨,到不死之身,到有靈氣、能使風雨,一直到天帝那一層就成了神仙。屈原到了第三層,已達到很高水準;据王逸說,是因“受道聖王”(從舜那裏接受了道),才登上縣圃山這座“神明之山”的。 讀者本可感覺到,屈原滔滔不絕地對舜談古今為君者之成敗及賢人葅醢的大道理,也不像來聽教導的,舜也未對他面授什麽機宜。大概正因如此,楊雄《反離騷》“横江、湘以南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将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累與”。句下張晏注很有意思地說:“舜聖,卒避父害以全身,資于事父以事君,恐不與屈原爲黨與”。張晏的意思是說,舜曾躲避其父對他的迫害,自保其命而已,從舜事父的態度觀其事君之德,恐怕不會和屈原為同黨之交。所以也不會替他拿主意解危難。不管他與舜之間有沒有更重要的交流或交流了什麽,都是隨漢代的作者或編輯們的猜想,我們後代的讀者實無法探求,所以我們最多只能正視一下,他來此“登之乃靈”的縣圃看到了什麽?
50 欲少留此靈瑣
接下去的下文是:“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王逸對此句中“靈瑣“的解釋竟是“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也就是說,上了昆侖山的縣圃,屈原沒遇上什麽神仙或天帝,卻竟然到了有連瑣花紋的“楚王之省閣”(指中樞政權機構)。經過幾番迷途未遠、復修初服、往觀四荒、陳詞重華、而神與化游,進入神山,心理上轉了一大圈,轉來轉去,又轉回原點了—他又回到楚王省閣了。這是不是做夢?夢登仙、夢升天,都會引出楚王。楚屈原夢魂縈繞的就是他所割捨不下的那位昏庸而固執的楚懷王啊。在整部《楚辭》中,以登天或登仙比喻登上朝廷見君王見天帝還有幾處。王逸不露聲色地讓屈原説確實很想在君王的省閣稍事逗留,來等待(須)君王有關國事的指導(“政教”);又説太陽卻又很快落下,馬上天就黑了,我的生命也快結束了--這又像現實感受的細節,不過都交織在荒唐的夢中了。不管怎麽說,至縣圃而見楚王省閣,從文理來説,連解釋成夢都不通,因爲寫陳詞於舜和離開舜而至縣圃,已經是幻想。所以,在縣圃又見楚王省閣簡直就是夢中之夢了。有學人在此等處引申出楚假屈原的所謂思其族源的情結,且認爲楚民族發源地就在昆侖山西、北諸地(崦嵫、扶桑、咸池等),實在有點想入非非了。可以毫無保留地說,研究屈原的“楚鄉”情結的學者們,完全是走入迷宮, 把自己搞糊塗了。有從顓頊開始的所謂楚民族起源的研究,實在是一種“考證在假的針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的僞命題。這個幻想太突兀奇絕、離題萬里了。
須知,所謂屈原者,只是編輯者假借楚名義生造出來的子虛烏有的人物!用來代替那位漢代的知識精英劉正則的!此之謂假楚而喻漢。所謂假楚,不單是借楚,而且是虛假地借楚,因爲楚國沒有與劉正則在學問、道德、器識、才具各方面旗鼓相當的人物,所以要虛擬假造一個;而劉正則因才具器識太遠過常人,曾有儲君之望,引起雄殘大志的漢武帝之刻毒的嫉恨,終于多方羅織罪名加以滅族之大罪。不但滅族,而且號令群下尤其是史官在各種場合不得提其真姓名,謂之滅名!這就等於要抹殺這個人曾經存在的痕跡。這“滅名”的決定, 几乎是空前絕後。這個決定, 顯示了這個做了傷天害理、滅絕人性之事的暴君對他是何等痛恨! 他本人作下如此不似禽獸更不如禽獸之事,又是何等的自私心虛!明知罪大惡極,還要毀尸滅跡,而且毀“事”滅跡。在那上層政治内幕極少為百姓乃至中下官僚所知的情況下,消息是非常封閉的。當時大概只有極少的大臣或史臣知其秘史。漢武之後,劉向至王逸的寥寥幾位有名或無名的編輯(其實也是史官)奉旨編輯楚辭。《淮南子》以其巨大的文化哲學包涵、尤其卓越的治國治民方略成爲漢代思想武庫的重要寶典,自不可廢。《淮南子》的姊妹作《楚辭》也不得不改頭換面而問世,連《楚辭》的名目也是假造的,它主要是漢人之作,經過編輯修改和潤色,利用“楚” 的兩種含義,雖假裝是楚國特產之辭賦,實是未必楚國之(“楚”)情的抒發。
例如,《楚辭》竟有這樣的定義:“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 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九辯章句敘》)。這裏,“宋玉閔惜其師,…故作《九辯》以述其志”是一個因果句;“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也是一個因果句。“故”字表示結果,其前之因何在?就在“咸悲其文依而作詞” 中的“悲”字,是以“故”字强調了這個本不顯著的“悲”意,而定義了“楚詞”(=楚辭)的性質,專門抒發悲苦之情的。所以此處對《楚詞》的界說,是給《楚辭》做了別樣解釋。“故號為楚詞”的原因,是劉向等“咸悲其文依而作詞”。豈只如此,悲痛艱辛酸苦凄慘哀愁創傷憂戚冤煩,都可遇“楚”而成詞,表達幾乎所有被殘忍折磨的冤枉委屈、憤怒懊惱、五内俱焚和肝腸寸斷,都是靈和肉之極端負面的刺激、劇烈虐待;臣之“懷忠貞之性”,偏偏“被讒邪”,唯一能寄希望的“君”又如此“闇蔽”;在極端絕望之下,靈魂發出的呻吟,以及已被暴君的高壓變了形狀變了腔調的同情,此之謂《楚辭》。王逸給《楚辭》所下的這個定義(另一個定義出自班固),應也得到注意。如果用這個意義來解釋《楚辭》,很多現代人都在不由自主地寫楚辭。閑話少説, 就此打住。大概受“楚鄉僞命題”影響了。
51 令羲和弭節
接上文,時近傍晚,我命將休。屈原乃“令羲和弭節,望崦嵫而勿迫” ,就是命令日神放慢速度,眼望他本應落進去的那崦嵫山,而不要太迫近它。王逸又説“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冀及盛時遇賢君也”。可見此處的屈原又是日暮年老, 來日無多,(請注意此人不是劉安太子,而是劉安本人)他想延長自己的生命來取得更多時間,以爲只有這樣才有希望再趕上興盛的時代而遇上賢明的君主。從時間上考慮,他升天而求神的路還很遠,上下求索也很費時間,所以他很想延長自己的生命。只是他延長生命的方法竟是讓日神慢行車、太陽慢落。用如此幻而又幻的物象來誇張事君之忠誠, 其忠誠還能是真的嗎?
52 道德不施
如上,王逸在注釋“望崦嵫而勿迫” 句時, 用了“道德不施”一語,來概指真屈原所處時代,實已至武帝時,當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已大致取代“文景之治”。其實重複地說,無論是黃老之學,或老莊之道,似乎都可籠統地描述或反映西漢文景時尚佔統治地位的以“道德”為標簽的官方治國方略。隨著中央集權逐漸加强,這種總體上利於小國寡民,不利於大國烝民,相對利於民權、不利于君權,利于同姓諸侯王分治、不利于皇帝集權的政策雖然被頗爲僥幸地堅持了幾代,已漸被大一統的封建帝國吞沒而消亡,至漢武時,尤其是對淮南王文人集團展開大屠殺的“淮屠”之後,“道德“ 已幾乎“不施”,國家政治的運作和變化,多靠儒家和法家(或稱儒法家)的縱橫捭闔了。
第十六段 東極飲馬 西極相羊
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須臾、相羊,皆游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墯,告我嚴裝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紛總總其離合兮(總總,猶僔僔,聚貌也),班陸離其上下(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僔僔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
段意:從在東極飲馬咸池,到至西極折若木拂日,一路煊赫威武,役使百神(月御、風伯、鸞皇、雷師、鳳皇),又遇上飄風雲霓,邪僻乖張。全部亮相神人乃至邪惡讒佞之著色,皆以效忠君王爲中心,溢濺著編輯者强加于諸位角色的忠君奸臣之濁墨。
作者:劉正則(其原文文字被改、文意也有被注而歪曲處)
要點:與日俱浴 以留日行 若木拂日 役使百神 紛總總其離合兮 上下之義
53與日俱浴
飲馬於“東極” 的咸池,是日浴之處, 屈原亦在此與日同浴以潔身。信哉其誇,果可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媲美。只是從原文實看不出來有“自浴潔身” 的意思。解釋原文,説些不相干的話, 有時是造情節、有時是編故事,有時簡直做論文,有時直接離題對某事物故意說寫些似乎不著邊際的話,都可謂別有用心。但出奇招唱贊歌,難免唱過火唱走調,反而失去贊歌之效。
54以留日行
“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意思是繫馬扶桑之樹,因而留住太陽,使它不能行過去,即不能開始從東到西的路程,日不得過,則時間停止,我因此可得長壽不老也。真是美麗的童話邏輯。限於當時科技發展水平,當代之人無權嘲笑這種人類童年的幻想。
55 若木拂日
《山海經•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倫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王逸正常注解了若木、須臾、相羊等詞語,然後就發揮想象,説屈原“言己總結日轡(即繫馬扶桑之樹),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恐怕制不住日,一年的時間畢竟還是得過去),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所以又轉而去了西極日落的地方,摘取若木樹枝),以拂擊日,使之還去(用來拍打太陽,使太陽回東方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權且自在游玩,來等君王之命)。所以依王逸之注解,屈原不但不讓東升之日開始向西走,而且還想以“拂擊”的方式,不讓走到西天的日落下,逼它直接回東方去。如果表達的是爭奪和珍惜光陰,是不是太誇張了?尤說他這樣做是爲等待君王任命,也令人解頤,是諷刺吧。
56 役使百神
作者在原文中之“役使百神”,應是神仙家雄奇瑰麗自由奔放的想象,象徵人對征服自然力及掌握自己命運的渴求,當然帶有原作者英勇的奮鬥和受難的感性色彩;這本是真屈原之本色當行。但經過至王逸爲止的編輯者任意塗抹為解,所謂百神幾乎成為儒家統治圈内官僚群(有忠有奸),多以君命為轉移。且看:月神望舒,“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諭君命”。鸞皇,“以喻明知之士”; 雷師,“雷為諸侯以興君”;“吾令鳳皇飛騰兮”,是讓“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俱共事君”。如此等等。由此又可看出這位屈原雖夢想上了天、入了仙,人間的一套君臣糾結卻一直牢牢地纏繞其意識、遮蔽其眼界、限制其格局。這種行爲確實很新奇,但并不是可敬,而是可嘆可惜;是編輯為假屈原加彩,所加之彩也只是强調其忠君情結。只是因爲他也胡亂冒領了真屈原的博學多識和雄傑胸襟,人們才很少這樣懷疑他。
57 紛總總其離合兮
“紛總總其離合兮(下接:班陸離其上下)” 與下文的 “紛總總其離合兮 (下接:忽緯繣其難遷) 重複。 不同篇章中有重複雷同的句子,尚可找理由證其合理性,現在同篇相近之文中就重複,應説是暴露了編輯者面臨一大堆文章而做選擇排列時偶見的疏忽。
58 上下之義
又,“班陸離其上下”這個句子,應謂飄風雲霓(比喻邪佞勢力)混亂分佈而飛上流下。王逸卻直接以“上下之義”代替了飄風、雲霓的上下運動或位置,這種過度的比喻,其本質仍是以喻體代表了本體,此處竟是直接以制度、道德觀念(“上下之義”)代替一種幾乎無法成喻的自然現象,這當然不是原作者的本心,而還是編輯之狡黠,不過是前文所謂忠信A、仁義A等手法的沿用或變用而已。實際上,看透了貫穿《楚辭》全文描摹楚假屈原忠信仁義的狡黠手段,就看透了編輯者專爲他設計的虛僞造作的忠信仁義;連楚屈原都是子虛烏有,他的道德能是真的嗎?他能有道德或者無道德嗎?
第十七段 高丘無女 下女可貽
吾令帝閽開關兮(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妒(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緤,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絜淨,閬風清明。言己脩絜白之行,不懈怠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
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下女之可貽(相,視也。貽,遺也。言己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
段意:(接上 “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的形勢)屈原欲見天帝,而閽者(佞臣)拒門,因世無明君,善惡不分,乃回到前文(第十六段)去過的昆侖山,往上濟白水、登閬風,仍是反顧而流涕,哀高丘無女,便轉向東方,及榮華未落之時而求下女。
作者:真屈原劉正則
要點:帝閽不納 高丘無女 遊此春宮 又是仁義A
59 帝閽不納
“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將上訴天帝,天帝的門吏卻拒而不納;真是世暗時昏,天上如人間。 只好結幽蘭而長立(也就是懷高德而徒然等待)。可見即使上了天,也擺脫不了人間的困境;仰對昏天訴說人間的苦難,而人天一揆,冤莫能伸。怪不得王注云 “有還意也”,大概就指到了新地方,還發老牢騷,好像回還到人間了 。果真如此,上訴天帝更有何益?所謂天帝不過人間君王的幻象而已,又哪用費如許周折?
60 高丘無女
“哀高丘之無女”這句話,依敘事的綫索講,本是“屈原”在昆侖山上渡過白水、繫馬閬風之後,“忽反顧以流涕兮”(陡然間回頭看而且流淚)時説的。所以,高丘, 應即昆侖山本身;高丘無女, 即昆侖山仙境也沒有他所欲求的女,這與楚國無賢臣沒有關係,而楚國真無賢臣也不用他去求。王逸注云此高丘乃楚之高丘,還説“女” 是喻臣,完全失去了敘事的邏輯,真可謂一種夢囈。況且,楚假屈原本身為臣而不見容,有何理由、有何資格為楚王尋求新臣?漢真屈原也無為漢帝薦新臣的資格和權限,大概本來稱臣於他的淮南客也面臨絕境了。
但“哀高丘之無女”顯示,即使在昆侖山仙界,也沒找到他希望找到的美女慧女仙女神女。這個失敗的哀嘆只能由漢真屈原發出了。因爲他之求女,是基於性愉悅的追求,通過運用房中術的練氣、導引等秘方,與美麗、高貴、智慧乃至仙聖的女性交接,自以爲可達到生命向仙人的提升。 男女交接本身成爲生命的享受和產生新生命的途徑,本來是極自然又極神秘的。作爲神仙家的作者把求女當成求仙的手段是不言而喻的。當然,他在求女時不但有凡人的情懷色欲,而且也想獨辟蹊徑,打通求仙得道之路。
即使原來的遊仙段落被截取改動,造成一些環節的斷裂,我們仍可看到由編輯者進行彌補和誤導而形成的、許多令人惶惑的問題。原作者在幻想或冥想中遊仙界之昆侖山時,心中懷有許多人間的不平、憂傷和希望。但以求女比喻求賢臣、求天下賢人、求同志,甚至求君,諸種導向,都説不通。無論是滿足人欲,還是通過人欲之調節,感覺上向求仙的目標逼近,求女行爲都屬於房中之術的各個層次的實踐。不要忘了。我們考出的真屈原劉正則,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天才、學問家、神仙家。其縱橫捭闔之天才,從《淮南子》及《楚辭》,皆可見一斑。百代以下,誰人可望其項背!他的眼界之高與地位之高,都使他能多方求女,而難以求得滿意者,與之共修仙體而臻仙境,也是自然的。
61 遊此春宮
“溘吾遊此春宮兮” 句下王逸注“東方青帝舍”。就是説,屈原忽然一下子從近西極的昆侖,到了東方青帝舍(雖未言東極,也在極東吧),説到就到。青帝,也叫東帝,劉長曾經自稱東帝。東帝又稱木帝、蒼帝。東方青帝舍,也可叫東宮,而東宮就也是太子宮,令人聯想到劉正則淮南王太子的地位。從四季言,東配春,故也可叫春宮。春宮又使人想到春畫和“謠諑謂余以善淫”,有時簡直是天地陰陽交歡、大行性放蕩的地方。這裏有眾多的“女”,尤其“下女”(王逸稱之為天下賢人),這當然與真屈原企圖通過房中術的修煉以成仙的奢望有關。換言之,《離騷》中的求女, 本質上就是求女本身, 所謂求賢臣、求君、求隱士等説法都是編輯在處理和注解原文時故弄玄虛。至少求仙的神仙家本人劉正則認爲,在滿足情興性欲之外,通過房中之術的修煉,可能有望成仙。
62 又是 “仁義A”
接下二句,王注謂到了東方青帝宮後,“觀萬物始生” 就是萬物“皆出於仁義”(也許真皆出於造物者卓絕的仁義);但説他 “折瓊枝以續佩” 就是“守行仁義,志彌固也”有點費解;大概“佩”(佩玉、或佩芳花) 就是“守行仁義“了,” 被“折瓊枝以續”的佩,則是在仁義上加仁義,即更堅定他“守行仁義”—在此瓊枝和佩都直接代替不同層次的仁義,説到底,仍是以喻體代替本體,這仁義還是前文所數見的仁義A。
又“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二句王注“言己既脩行仁義” 應是繼續强調從“折瓊枝以續佩” 解出的“守行仁義,志彌固也”的意思。“思得同志” 用來解釋 “求下女”,大概是通過房中之術求仙的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説到作者的年齡, 我們不得不再次肯定,這是劉安之子劉正則的特徵。“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這與“思得同志”一樣是捉弄讀者, 尤“與俱事君”,更是無根之談(連自己都不被接受,再找人事君來豈不是招罪)。下女,應非代表天下賢人,而是指非貴族、非神仙、地位低的普通女子—只要機緣凑泊,也可成爲他聘請或追求的對象。把求女强行解釋成爲君求賢,王逸大概也會料到後代讀者不會相信, 這似乎是他故意賣的破綻。只是好多後代近代研究者,都被前代權威 ,尤洪興祖和朱熹,最早的全面注釋楚辭的專家—所誤導了。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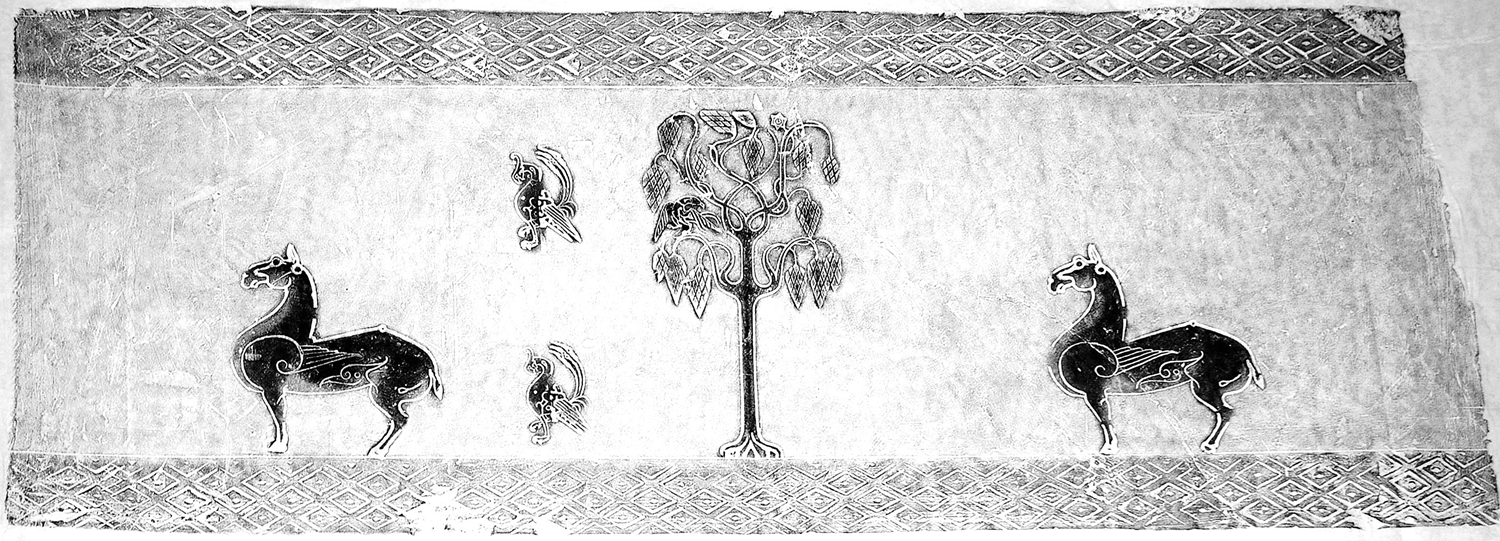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