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生活的城市里,每天以四百辆新车注册的数字增添着城市街道的压力,每当高峰时,整座城市都缓缓蜗行在几条主要干道上。然而,即使如此,依靠公交车出行的人依然是大多数,尤其是那些挥挥手告别村口大槐树的人们,进入城市便成为乘坐公交车的主流。
今天的公交车内,一种特有的声音成为城市的一景,那便是此起彼伏的彩铃和操着各种方言或变调普通话的打电话声响。这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各种手机彩铃声响和方言土语体现着多元的声音。譬如有位少妇对着电话用夹生的普通话理直气壮地说:给了我一块市场,这两天很忙,所以没时间给你打电话,云云。有一位分不清什么口音的男子,张口便骂上了,每说一句话的开头必先来“妈了个”看来是对方欠了他的钱。还有嗲嗲的撒娇声,也有粗门大嗓咋咋呼呼的。真正的是各种性情各种方言的大荟萃。其中,最多的是本地方言,就像多年前我们到其他城市,公交车上就是一场当地方言的讨论会一样,偶尔冒出一个不同的声音,人们便会觉得很突兀,同样,操着外地方言者也会觉得很孤独。方言,在一些大城市,犹如标签一样,注释人们的身份。
多少年了,人们试图用普通话一统南北,却始终难以磨灭乡音的魅力。
突出的是影视作品,今天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于他们小时候所听过的粤语香港电视剧《陈真》《霍元甲》等插曲记忆犹新,且张口能唱,因为那些歌曲作为一种时间背景的见证,附着着若干他们小时候的美好记忆。近期影片《疯狂的石头》中的方言,成功塑造了一个青岛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见媒体与影视作品的影响。
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方言在社会的进程中,几次都顽强地扮演着自己特殊角色。譬如粤语。广州、香港,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而经济活动是哪里有空间便向哪里渗透,从南向北渗透过来的首选是语言,随之而来的是媒体语言的传播与文化产品的流行,甚至不仅语言被模仿,且操粤语者的行为举止也被模仿。这种“东施效颦”现象令人慨然的同时,便对汉语方言产生某种疑惑,粤语是若干汉语方言中的一种而已,何以能够覆盖全国?然而这种借助经济强势而来的文化毕竟是短暂的,很快便在人们一片“鸟语”的唏嘘中渐渐淡去。
也有相反的例子,譬如东北方言,至今人们分不太清东北三省之间的语言区别,但是太远的历史不必说,仅仅“九一八”这样一组数字,便是曾让一个民族撕心裂肺的疮疤。东北曾是我们的粮仓,是重工业基地;然而,曾几何时,东北口音却令人们不寒而栗,几件恶性案件令东北人在人们心中威信大跌。近年来又发生了河南人被某城市所歧视的事件,来自中华文明发源地的中州人,不知道经济时代人们何以就可以转脸不相认?
穿衣打扮可以与他人没有区别,而方言往往一时难以改掉。所谓“隔河不同俗”,不仅说的是黄河东西两岸语言的不同,还说的是汉语在辽阔的大地上因地域的不同和多年战乱,人口不断迁徙而形成的方言与习俗的不同。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方言是人们生存环境的胎记,据考证,汉语的方言主要由秦晋两地的方言与其他地域的方言融合、传播、发展而来的。而方言始终存在着差别的同时,也一直存在着共同语。共同语的书面形式虽然自秦统一,而口头的共同语在春秋时代便形成了,那时叫作“雅言”。《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平时说方言,但在读《诗》、读《书》、行礼的时候,则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
汉代扬维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中,称共同语为“通语”,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称共同语为“天下通语”,明代张位在《问奇集》里称之为“官话”,辛亥革命以后称之为“国语”,现在称之为“普通话”。可见共同语在两千年来一直被人们所提倡和应用。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通讯落后的时代,家书抵万金,而没法写信的岑参便只能让使者带口信了,这口信是否方言虽然难以考证,但是大唐在那个时候往西去的语言是以秦地方言为主基调应该是无疑的。在有语言活化石之称的地方戏曲中,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所流传着共同的梆子戏曲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也只有这种相同的“传语”才具有那种可以意会的报平安的魅力。吟诵着《乡愁》的余光中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多次引用“乡音未改鬓毛衰”的诗句,作为“在异乡为异客”的余光中,方言在这里表现出了难以取代的魅力。
青岛市自建埠以来便是一个移民城市,各种方言荟萃,年久了便形成了青岛方言,除了其声调之外,其有意义的是创造产生了具有独特含义的语言。毋庸置疑的是普通话在传播与沟通方面的作用,两千多年来,祖先们始终在倡导公共语,但是,方言的作用却也始终难以磨灭。在孔子的家乡曲阜,人们依然在说着讷讷的方言土语,但是不影响他们继承孔子“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为人之道。因此,我们不妨也如孔子,操起两套语言,一套是“雅言”,也就是“普通话”,另一套便是改不了的“乡音”。
公交车上是方言集中的地方,而说什么话主要在于对象,只是公共空间里,无论方言还是普通话,都要文明才好。
韩嘉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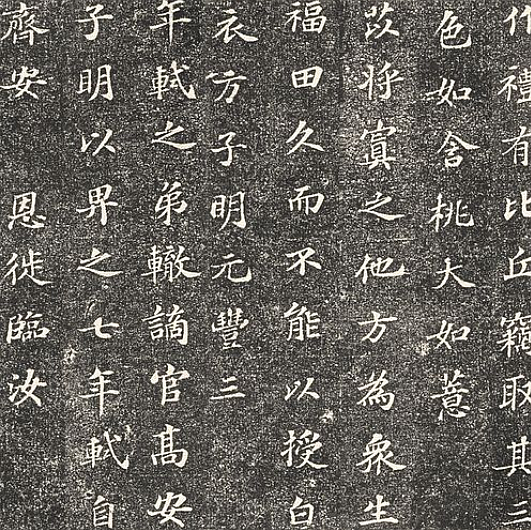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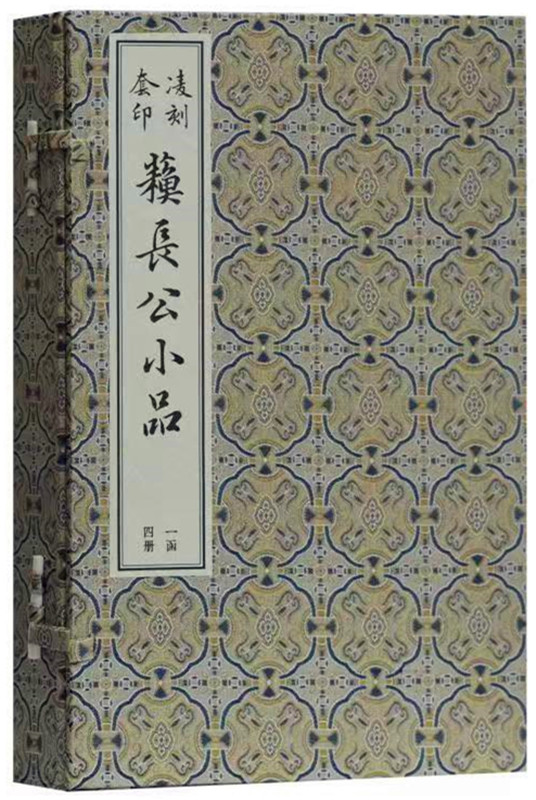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