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秋天,我们娘儿仨在老家农村安家了。房子还是我家的旧房子。原先借住的那户人家搬走了,由生产队上管着。我们回来,就还给我们。房屋更破旧了,只好先住下再说。早先,青岛这边的人为了能让村里收我母亲,与大队干部几次协商,把我也随迁,又加上将给我母亲的安家费不给个人,而是放在生产队上,由队上支配。这笔钱究竟有多少,我们始终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名目从厂里领出来的钱。但我母亲知道有这么一笔钱,所以回到村里以后,母亲就找到队上,要求用这笔钱给我们修理一下房子,再买一些在农村生活必须有的东西。队上也同意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由生产队上的姓孟的保管员,带着我分别到了西边8里路的故城和东南也是8里,但是过河了属于山东省的四女寺,去了两趟,买回来几件生活用品和几件农具。
生活用品有一口大锅,当时不说直径多少厘米,农村人叫几印(不知是否这个字)的,我们买的是8印的,似乎是最大的了。回来后安在堂屋的灶台上。一般家庭就这么一口锅,贴饼子,?红薯,煮菜,烧水,都用它。一只风箱,那时农民的燃料主要还是庄稼的秸秆。还有一只大水缸和2只铁皮水桶,一根扁担。这只大水缸很大很重,高约1.2米,直径约一米。我们推着一只独轮小推车,是那种旧式的,车轮是铁的,直径约有40厘米,装在前面,后面车身上延伸出两根车辕。把大缸扣在车身上,从8里外的四女寺运回村里来。
运这个缸无比费力。你想,这只水缸总有150-200斤重吧,而这种小推车,重量几乎都落在后面。人要用力抬起车辕推动车行走。那位孟保管员在车辕上拴一条绊绳,绕在肩上同时承受一些重量,让我在前面用一根绳子拉车。我们十分艰难地把这只水缸运回来。
生产工具方面,买了一把铁锨,二把镰刀,一把锄头。过了一段时间,队上又用我们的安家费买了一批红瓦,安排人铺到房顶上,初步解决了漏雨的问题。
我们回到农村的时候,好在正是秋收时节,生产队上打下什么粮食就分什么,我们也学着乡亲们把分下来的玉米锤,在院子里晒干,把玉米粒弄下来(用大锥子穿,用另一只脱了粒的玉米芯搓),再骑自行车到加工地点,去粉碎成玉米面,回来蒸窝头或贴饼子,做口粮。
在青岛的父亲心里盘算着一家人的未来。他有危机感。既然整了母亲,父亲作为反革命家属也必然受影响,何况他自己四九年以前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这种危机感随着对他工作的调整,而更加急迫了。事情是这样:父亲从参加工作一直在职工食堂工作,他工作勤恳,不计得失,在与同事交往方面,一向抱持着吃亏是福的观念,从涨工资到评先进,处处让着他人。上班总是早到晚退,自觉加班加点,所以他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文革”前的一次涨工资,大家一致意见,给父亲涨了两级工资,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后来父亲长期担任食堂成本核算员,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关键岗位,关乎部门的总体效益和经营结果。说明父亲的工作表现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肯定。
母亲被遣返后,食堂的主管部门厂总务科新来一位副科长,是转业军人出身,他知道父亲的情况后指示食堂负责人:“他老婆是反革命,遣返回乡了。怎么能让他在食堂这种关键岗位上,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这样就不让父亲在食堂干了,把他安排到总务科下属的维修组。这个组是由一些木工瓦工等人组成的一个小部门,负责厂里和家属院的房屋等维修工作。父亲也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就让他跟着这些师傅当小工。
这个活比食堂的工作轻松不少,往往是上班后跟着某个师傅到哪里去修理某方面,上班好长时间才出发,到了那里也许半个小时就把活干完,然后就找地方休息抽烟闲聊,混到下班时间回家。当年大锅饭体制下,都是这么干活的。
但父亲想,母亲当年的仇人,以及厂里那些乐于整人的人,不会放父亲在一个小部门就不管了,恐怕还要斩草除根。父亲怕的是,接下来找个借口把他也赶回农村,一家人生活可怎么办?
父亲想到了支援三线,摆脱青岛这些人。这些人了解母亲也了解父亲,他们长期对母亲和父亲有成见,不会放过我们家。而如果到了一个新地方,又是小地方,可能会安全。再说,支援三线是当时政府号召的,去了之后,是进步光荣的表现,这样或可免于灾祸。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他有生活的智慧和果断。他不固守一个地方。当时搞三线建设,大多数城里的工人并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到小城市去。父亲主动提出要到三线去,也是顺理成章。
通俗地说,三线就是指小城市,支援三线是政府让大城市的工厂到小城市,帮助新建工厂,大城市的厂去技术人员,在当地招一部分工人,建起工厂来。青岛由于是轻纺工业发达的城市,有10多个国营的纺织厂,因此就让分别到山东内地的一些小城市或县,帮助建厂。让大城市的工人到小城市,所谓三线城市建立新厂,上面是出于战备的考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备战备荒”。
青岛各厂支援三线的工作统一由市纺织局某部门负责,因此父亲报上名以后,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与父亲联系沟通,看青岛联建的三线工厂哪里要人,再问父亲是否同意到那个小城市去。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大约是1969年上半年),设在山东北镇(当时的惠民地区驻地,今天的滨州)的青岛帮建的棉纺厂要人,青岛这边就通知父亲做好准备离开青岛到那里去。但不知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又没有消息了。
时间到了1969年秋天,通知父亲山东临清棉纺厂要人。前面说过了,父亲是怕待在青岛被赶走,尤其是进入1969年以后,又兴起了“疏散运动”。那时一方面是强调备战,一方面是城里无法解决那么多人的口粮和就业问题,所以要求各地把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及家属,迁回农村去。既然有这种运动,那么首当其冲的还是家庭有问题的人。我母亲已经被遣返了,把父亲和剩下的人也赶回老家去,正是名正言顺。所以父亲特别担心此事。一说临清可以去,父亲很高兴,也是因为临清地处鲁西北,离我们老家村180华里,往来也方便。所以父亲立即答应了。在办手续的过程中,负责的人又问父亲,家里是否有够年龄的子女,可以带去安排就业。这真是个好消息。父亲事先不知道有这政策。我姐姐当时正好前一年初中毕业了,正在上高一。实际上学校也不正规上课。
这样,马上办理我姐姐就业的手续。在1969年秋天,我父亲就带着我奶奶,大弟弟搬家到了临清。姐姐就业,先期派往石家庄棉纺厂培训,几个月培训结束,就到临清棉纺厂工作了。父亲到棉纺厂后仍安排到职工食堂工作。
来临清不久,厂里给他们分配了宿舍,里外两间,是厂里新盖的宿舍。红砖楼房,四五层高吧。一个单元三户,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水管。在当时这是整个临清最好的住房了。临清是聊城地区下属的一个县,棉纺厂建在县城里。生活水平无法与青岛相比。父亲带全家到这里来,进一步受迫害的威胁,不能说没有了。但比在青岛,总是减轻得多。虽然时间长了,厂里一些人,包括个别领导,也因为我母亲遣返回农村,以及父亲历史上有“污点”而另眼看待,但总体上比青岛原来单位强多了。只要父亲不犯什么大错误,几乎就不存在被赶到农村的威胁了。
姐姐也挣钱了,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考虑到小弟弟年少,在临清受教育更好,所以,父亲到临清后,我小弟弟基本上就在临清生活了,虽然户口还在农村。
由于老家和临清离的比较近,两边来往方便多了。从临清回我们老家,坐长途汽车到德州,从德州再回村里。从老家到临清也这样。我是骑自行车来回的时候多,180里路,骑车要多半天时间。顺风大概每小时能骑行25-30里。如顶风,估计也就是20里,甚至更少。我曾数次往返临清和老家之间,顺风时,从临清出发,中午刚过就回到村。下午接着下地干活,那时很看重挣工分。而赶上顶风,就几乎要一天的时间,骑行非常吃力,回到家也非常累。
临清是一个县城。但它历史上曾是一个比较繁华的都市。明清时期,漕运发达,临清是运河上重要码头和货物转运站。政府在此设立税务机关“钞关”。旧址修复,现在成为临清著名景点和历史遗存。那个时期,南来北往的客商云集于此,带动商业十分发达,有“小天津”之称。家乡村里老一辈的人中,很多人干过“拉船”的活,就是拉纤。从德州到临清,因是逆水向上游行船,故需要纤夫拉船行进。
清末,铁路兴起,漕运衰落,临清的地位不复从前。四九年以后,临清短暂设市,后来降格为县了。但由于传统的原因,到“文革”我们家在临清时,仍留有相当的传统的东西。比如,商人逐利,头脑要精明。有些人因此被认为狡诈,人称“临清猴”。又善于交际,嘴巴很甜,喜欢高一辈称呼人。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见到我这个小伙子,也一口一个“叔叔”“叔叔”地叫。让人不大习惯。
还有一点,临清毕竟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生产的某些生产生活用品,比别处多。我在家乡时,往来临清与家乡,记得在临清买过自行车的链条和轮盘,这在我们那边很难买到。也给乡亲们买过。那时没有拆迁,到处还是老房子,依稀可见旧时商铺林立、买卖发达的街市情景。旧房子的基础,还有人家的院墙,有不少是用当年临清供给朝廷用的大青砖垒的。上面刻着工匠、监制人的名字。现在这东西恐怕早成了文物了。
世事的变化无法预测。我们家待在临清直到1979年发生改变,这年母亲回到青岛退休,小弟弟顶替母亲到厂上班。又过了一二年,父亲在临清退休,因为母亲在青岛,政策允许,他的户口也迁回青岛。而姐姐在1974年结婚,后来她与姐夫先是调到聊城棉纺厂。于八十年代初期调回了青岛。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也于80年代中回到青岛。这样临清就只剩下大弟弟了。他在那里结了婚,安家在那里。我回到青岛后,也曾想办法把大弟弟一家办回青岛。种种牵扯,中途放弃了。
我最近一次回到临清,与大弟弟一家见面是2021年。我们去了国棉厂旧址和家属院。厂房大多荒废了,从家属院到厂区的大道,原先上下班时间,人流如织。到了晚上,厂外的工人俱乐部、灯光球场热闹非凡。现在只剩下一片荒凉和岑寂。不过最近一二年,当地把旧厂区开发成“国棉厂文化创意园区”,恢复仿建当年的一些建筑和场所,借此满足人们的怀旧心理并发展经济,也是一件好事。
(11)吃粮是大问题
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似乎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粮食吃,吃几乎不是人生应该考虑的问题。我在回到农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无怪乎古时某皇帝,大臣向他报告,灾民没有粮食吃,他却说“何不食肉糜”。
写到缺粮,我在这里要插叙一段乡亲们口中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的事。
我们回到村里,与社员们共同劳动,时间不久,就发现几乎人人都会说到1958年“大跃进”之后,成立人民公社,开办“大食堂”(即社员集体吃饭,不允许各家开伙),而后饿肚子,人人吃不饱,饿死很多人的事。
综合乡亲们的说法,1958年虽然是个丰收年,但由于上面征粮太多,实行大食堂吃饭,各家不允许开火。大食堂供给的饭量根本不够吃。村里干部贪污腐化,加重了缺粮。接下来三年旱涝灾害。普遍吃不饱,得病的人多,出工的人少,农业产量大降,造成严重缺粮,以致饿死人。据乡亲们说,那三年中,我村以及周边村里老人大部分饿死了,青壮年因病因饿也死不少,以至有的村,人死后,没有人抬棺埋葬。
我们小队一户人家的老人(男性),临死前一直喊:“我饿啊,我饿啊。”死时手里攥着一块半干的萝卜。不知几天没有粮食吃了。这是他的邻居亲眼见的情况,说给大家听的。我的东邻,我们关系很好的我喊他大哥的,他的父亲当年饿的瘦成没有人样了,走路常常重重地摔倒到地上。不久就死了,也应该算是饿死的。
以上饿死很多人的事,是大家百口一词,异口同声地说的。普通社员说,村干部也这么说。可能是不过几年前的事,人们记忆犹新,死的人都是他们的亲人或邻居,悲惨的场景造成的心理冲击还没有完全淡化,人们还心有余悸,所以经常被提起。我们刚回去,听到这些话,感到很震惊,这不是很反动的话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公社,怎么能饿死人呢?然而,说这些话的,大多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
下面引用官方的记叙。《故城县志》记载:
168页:“1958年……9月全县即实现人民公社化。……由于急躁冒进等严重脱离实际的做法,……加之自然灾害严重,造成1959~1961年的农业生产显著下降,人民生活遇到暂时困难。……通过贯彻上述文件,全县制止“左倾”错误,扭转了农业生产的继续滑坡。是年(1962)全县农业逐渐好转,至1966年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生产水平。”
574页:“解放以后一段时间内,农民粮食占有量较少,吃粮处于紧张状态。公社化后,农民主要从集体分配粮食,最少者为1961年,年人均口粮123.5公斤,日均0.35公斤。”
20页:1961年“10月,上级拨付救灾款14万元,口粮33.9万公斤。”“12月中旬,沧州专区支援故城粮食239.5万公斤。”
132页:人口变动表。1949年人口死亡率11.69‰。1959年,12.32‰。1960年,20.64‰。1961年,26.23‰。
但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留待有心人去考证吧。
我小的时候,跟母亲在乡村生活,母亲是教师吃商品粮,我们不愁没粮食吃。到青岛以后,即使经历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间短,而且终究还是基本能吃饱,只是吃的差。
回到农村,尤其是1968年秋天随母亲第二次遣返回村以后,随着生活的时间长久,越发体验到吃这个人生的大问题。当然不只是我们一家,乡亲们人人如此,家家如此,去年如此,今年还是如此。
收成常常只够半年或多半年粮,甚至连半年都不够吃。一般麦收分到的麦子,只够吃一个月,而从麦收到秋收要3个月。秋收的粮食一般只能吃过冬天。过年以后到麦收来到的3个月,又是饥馑的季节。俗话说,无米下锅。我们家有父亲的支援,没有这种情况。与我们一个小队的社员家庭中,据我的观察,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长年缺粮。这些家庭往往是劳力少,分得粮食少,又不善通过其他途径得些钱,买粮食。
说到卖点鸡蛋换些钱,这是大约一半以上家庭来点钱的唯一途径。乡亲们有戏言:红薯面子当细粮,鸡腚眼子当银行。农民们一般家里养十几只鸡,多是母鸡,平时涮锅的泔水,碾米剩下的米糠等拿来喂鸡,下了蛋自己舍不得吃,积攒一二斤就卖到村里的供销社代销点上。卖的钱首要就是买家里点灯用的煤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农民家里很少用酱油、肥皂。基本上没人刷牙,也就不用牙膏牙刷。
缺粮的季节里,邻居家大婶做饭时候,常手拿一只瓢,来我家,对母亲说:“他婶子,家里又没粮了。”母亲就接过瓢来,从我们家的粮口袋里给装满瓢。有了粮食时,她会再还回来。吃粮几乎全是粗粮。当然收下麦子的季节也吃白面,但由于农民没有余粮,因此也就没有办法掺和着吃。只能收下麦子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吃面为主。秋收以后的大半年就只吃粗粮了。说到吃面,很多家是把麦子全磨了来吃,也就是说为了节约,整个粉碎,不筛出麦麸。
粗粮中以玉米为主,有三分之一的高粱面,秋冬红薯是主要的粮食。我们家乡种红薯比较多,是因为红薯对土肥要求不高,产量也比较高。吃红薯能使人虚胖,所以每到冬天,人们往往脸上貌似长不少肉,习惯上开玩笑说叫“红薯膘”。还有一点,红薯入肚消化比较快,人容易放屁。而放屁出来的气味又全是红薯味。晚上,以小队为单位,社员都要到队上记工分,小队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就在牲口棚里,饲养员睡觉的屋里,有一张破桌子一个破板凳。一般常聚集着10多个大人孩子,每人都放屁,那种特有的气味也就散不出去而弥漫在室内的空气中。相同的情况,全大队开会时,5个小队,开大会就在大队部里。这是一处三间高大的房子,以前是村里地主家的,土改时,地主被赶出去,做了生产队的办公室。原先这是一处有东西厢房的大院落。我回到村里的时候,只剩下北房三或四间了,厢房门楼院墙都没有了。大队部的三间房子,只有东间还保留着门,另外二间就是敞开的。开大会时,村民们就挤在这三间房子里,没有桌椅,全是席地而坐,约能到会百余人。农民劳动辛苦,出汗多,又不常换衣服,常年不洗澡,冬天再加上人人放红薯屁,空气之龌龊可想而知。古语有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玉米面的窝头尚可吃,高粱面的窝头或饼子很难下咽,而且吃下后,消化不良大便不畅,是很不舒服的事。生产队产的粮食不够吃,但公粮是每年必须交。交多少我不知道,这事队长和保管负责。但那时人人知道的事是每个队都瞒产,千方百计地向上汇报收成不好,以达到少交公粮的目的。交公粮是到8里外的故城粮库。队上收了粮食,脱粒后在场院里晒干,装到口袋里,过秤后由几个社员,一般是壮劳力,装到小推车上送到粮库去。我参加过多次送公粮。一般每次去三四个或四五个人,每人装上三或四口袋粮食,大约是三四百斤。这样大约每次送交1500-2000斤的样子。
我们用的小推车是橡胶轮胎的,直径约60-70厘米,车轮安在车架子中间,两边装东西,这种车子重量在车轮两边,又低一些,比过去旧的车,就是我说的我家安家时,队上保管带我买大水缸的那种,要省力和方便操作。
这种小推车是主要的生产工具,我回到家的前几年,我们家没有,另外我年龄小也驾驭不了。几年后,大约在我十八岁或以后一点,我们家就买了一辆这种小车,它从此就长年伴随我左右了。生产队里劳动,几乎天天用到它,推土推肥推种子推庄稼,到故城德州推化肥,到集市上卖菜等全用它。
推着粮食到国家粮库交公粮是很累的活。队上干部基本上都不跟着去。这样,我们几个青年人,到了镇上,往往是其中年龄大一点一位哥们,提议大家搞点小钱花。找到一家茶馆,从粮食口袋里倒出二三十斤左右,卖给茶馆。每人大约能分一二块钱的样子。事涉违法。然而集体的东西,不沾白不沾。大家都这样想和做。
与乡亲们推着独轮车到国家粮库交公粮,大多数情况下是沿运河大堤去和回。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记叙推车情况以及心情。现从中摘录几段:
沿着这条河堤路,我与乡亲们多次在夏天秋后推着独轮车去8里外的镇上交公粮。这是个力气活,必须派青年劳力去。粮食打下晒干后装进大口袋里,每个口袋装100斤左右,每人推3、4袋。如果是4袋正好车架两边一边放2袋。如果是3袋,就两边各放一袋,再横到车梁上一袋。木质的车架被压得吱吱响,车轮碾过坑坑洼洼的土路,带起泥土。我们这些推车人穿着家织的粗布衣裳,脖子上搭条同样也是土布做的汗巾,脚上是家做的布鞋,绳子纳的底子,踩在地上,留下特有的花纹,煞是好看。肩膀上使用一条绊绳,绊绳两头扣在小推车的两个把杆上分担手的重量。
推车时双手要与身体协调,保持车轮上方两边力量的平衡。在此基础上,用肩膀、手、腰、胯、脚的力量,通过手握住车把杆和肩上的绊推动车子前进。推着几百斤物品每小时也只能走5、6里路。到了镇粮库,验粮、过磅、扛上高高的粮堆倒下粮食,任务就完成了。此时人人一身臭汗,个个饥肠辘辘。掏出带的饼子,找个茶馆烩一烩吃,再喝上一大碗水,就又启程往回返了。回程就轻松多了,一路上,大家开着玩笑,时不时说些淫秽的笑话,吹着河堤上凉爽的风,像归巢的鸟向自己的村子走回去。
送公粮,走8里来回16里路,用广东话说是“毛毛雨啦”。推化肥、推煤、卖菜等,往东30里来回60里到德州,往西40里来回80里到我们的县城——郑家口,往北50里来回100里到王同火车站,都走过。都是当天去当天回。
推着几百斤东西走几十里,一步一步地量过,一步一滴汗地踩过,需要的是一种忍耐的精神。明知是苦,明知是几乎不能承受的沉重,明知推了这趟还有那趟似乎没有尽头的苦力,但只能无奈地接受、无奈地忍受、无奈地前行。
仿几句海涅《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的诗描摹一下吧:
车轮在转,车架在响,
我们推车,日夜匆忙——
苦难的日子没有尽头,
我们只能忍耐没有悲伤,
我们推,我们推!
2004年6月27日
胆子大的人,在收获的秋季,会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到地里偷生产队的玉米锤(我们家乡叫玉米棒子)。其他作物不好偷。为了保护生产队的粮食,大队上长年安排一二个人专职看庄稼。他们白天不用下地干活,大队上给记工分,晚上到地里巡逻。抓住偷粮食的就带回大队部审问处理。我在家几年,经历二位因偷粮食而被抓住的。一位青年人,他父亲是四类分子,所以他被抓住后受到相当的皮肉之苦。据说,除了被用棍棒殴打,还被吊到房梁上。另一位是中年人,家里有五个孩子,就他一个人是主要劳动力,生活困难。他夜里去偷队上玉米被抓后,第二天用绳子绑了他,脖子上吊着用绳子穿起来的玉米锤,押着他在村里的主要街道上游街示众。这个场面我亲眼所见。只见他光着膀子,低着头,双手被绑,大队上专职看庄稼的人牵着绳子引着他在村里走。我看到他满头大汗,很狼狈也很疲劳的样子。游完街,就放了他。下午就又跟我们一起到地里干活了。大家谁也不提这事。一定程度上同情他为了一家人吃粮而铤而走险,实属无奈之举。还有一点要交代。这位因偷玉米棒子被抓游街的社员,是烈士子弟。他的亲哥哥,参加解放军,攻打太原时牺牲,是在册的烈士。我在家乡的前几年,他们兄弟的老母亲还在世,不确定她有没有享受烈属的经济方面的补助。她和乡亲们一样,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去世。
(12)买粮食、换粮食
我们这个生产小队,有人口约30户,120~130人。土地约有300多亩。这样算下来,人均不到三亩。由于产量低,几乎年年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除了节省,就只有买了。在省的方面,一半以上家庭在冬天,没有太累的农活,就吃两顿饭,而且以粥为饭,没有干粮。粥,我们那里叫粘粥,玉米面或高粱面加水熬成。有的家里只给下地干活的男人吃干粮,妇女孩子只喝粥或吃点红薯。
说到买粮食,哪里来的钱呢?指着生产队上一年一度的结算,即使劳动力最多的家庭也分不多一点钱。印象里我们队前面讲过的H姓一家,就是老爷子是四类分子的那家。当年他四个儿子都还没结婚没自己过日子的时候,有一年年终结算,他家分到了100元左右,这几乎成了一件多年后大家还常议论的大事。
生产队上的钱从哪里来?一是卖粮食卖棉花,还有西瓜等的收入(据说交公粮不给钱。在这之外,属于国家统购的粮食、棉花,卖给国家,国家按规定价格给生产队钱);再就是靠我们村里的砖瓦窑每年分的钱。但生产队每年的花销也不少。大致有:买种子化肥浇地买柴油等。除去开销,用于分给社员的不多。所以买粮食要指望生产队分钱,基本靠不上。那就只有千方百计地自己解决了。
在当时,农民们还被允许保留一点自留地。农民们就拼命利用这有限的一点土地,尽量种些经济作物,以便能换些钱来买粮食,买其他生活必需品。其他大的花销,也要靠数年积攒来准备。如盖房、娶媳妇、为老人准备棺木、打发老人等。
穿衣是自己织的土布,很少有人家买衣服买布料。那时姑娘订婚,一般是男方为买几身衣服布料。再有的开销是学生上学要买书本铅笔等,这也是重要的开销,所以“文革”时期,我在农村时,一般家里的孩子上完小学就下来,这个年龄人也长大一些,可以帮助家里干活了。
有些生产工具需要用钱买,像前面说过的我家买的独轮车等。
在自留地里,村民们一般是种一些早成熟的鲜菜瓜果一类,可以多卖点钱。那时没有大棚种菜,都是天然,要靠时令。农民们就尽量赶早,精耕细作,多施肥,勤浇水。
有一年,我们队上一家人在自留地里种了一种脆瓜,这种瓜不甜,但成熟早,所以他们家也卖了一些钱。也有家里种棉花的,也是可以卖钱的。那时,国家对于棉花实行统购制度,收下来后只能卖给国家,不能私自加工出卖。
也有人独辟蹊径而赚了钱的。像我们队上一位姓时的,他当过队长。某年他在自留地里种小榆树树苗,虽然生长期要长一些,大约需要两或三年的样子。长到手指粗,七八十厘米高的时候,就可以卖了。记得他当时卖的是一角钱一棵。树苗种的很密。他家的自留地里种了几千棵。这样一下子就有了大几百元的收入。
看到他家赚到钱,其他村民也种起榆树苗,后来价格就不断回落,不值钱了。所以早看到商机,比别人先行一步才能赚钱。就像当代香港的富豪李嘉诚,他所以被人称为“李超人”,就是能先于别人看到商机或危机。
我们村的这位姓时的村民,在别人都大种榆树苗的时候,他养起了老母猪,下崽来卖。又赚了一大笔钱。总之,在当时,单靠生产队里分配,是富不了的。只能自己想办法。但也有问题。在自留地里种东西和在家里养点家禽家畜被允许。但搞其他,当形势紧一些的时候,就可能挨整挨斗。
当时也有些人,从事一些商贸活动。比如贩卖一些东西,或凭借手艺干点活。但做一点可能问题不大,时间长了,别人发现你干的大了,就可能出事。还有一个前提是如果因此耽误出工,就可能出问题。
我们村里别一个大队,有位仁兄,专门到集市上买旧自行车,回来家后进行一番打磨修理,磨掉锈迹,上点油,换换不好用的零件等,然后再到集上卖,每辆车就可能多卖个5块10块。但他后来,被村里批了一顿,不敢干了。我一个亲戚,是外村的。也是因为抽空到处贩卖点物资,而被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挨了一顿斗。另有胆子大的,贩卖化肥。我知道我们村有人从当地想法购入化肥,坐火车运到东北去卖。具体能赚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
为了省钱,用同样的钱多买到一点粮食。我和乡亲们除了在当地的集上买粮食,还到过临近的县,如山东恩县(今山东平原县恩城镇),说是70华里。写此文时我用高德地图查了一下是36公里。还有一次是到山东陵县(现属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40公里。这是比较远的,到恩城往返140华里,到陵县来回160华里。都是当天去当天回。但因为远,所以要下半夜就动身。去的时候是空车,轻松些。到了那里集上,经过挑选,买好后,装到带去的口袋里,放到自行车上,一般都是买一百斤左右。回来就比较吃力了。如果再遇上顶风,是十分辛苦的。
自行车骑行,去的时候能平均15,最多20华里吧。也需要四小时左右,而驭上粮食,最多能骑行15华里,就要五六个小时。大部分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骑行起来吃力得很。
有一次,约有晚上八九点了,我们还骑行在回村的路上,是无月的黑夜天,几乎看不清路,人也饿了渴了,我们三四个人,常有人摔倒,要大家停下来,帮他扶起车。远处看到几点亮光在一片的黑暗中,很令人怀疑是不是鬼火,大家都有些恐惧。近了才看清,是路旁的一所学校,一二间屋点着油灯。我们停下,到屋里讨了水喝,又继续上路。
还有一次,也是驭着买来的粮食,夜路往家赶。一个乡亲的车越骑越沉,实在蹬不动了。下来看看,链条上、齿轮上沾满泥。怎么办,又没水冲洗。有人提议,用尿冲洗。于是大家依次上前往链条上齿轮上尿尿。暂时解决了困难,勉强骑到家。
除了在本地买粮食。我与乡亲们有一年还到山东南部去换粮食。用我们当地产的土布(也叫粗布)到枣庄一带换粮食。多年以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记录这事,现从中摘引几段:
一年春天,家里瓮中无米。无奈,只得加入了“南下”的大军。原来,我们家乡是产棉区,民间都织土布,逢到灾荒年景,就用它们去鲁南换粮食。说起来也是互通有无,鲁南一带粮食多但穿衣困难——那时买布需要布票。
我们一行四五人,每人用个破包袱包着一丈二丈土布,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德州,傍晚时爬上了南去的运煤的火车。一夜颠簸,第二天上午车停薛城,我们下了车。
历尽艰苦,大家在数里外的村子里换到了粮食。我记得我年龄小(当时我大约十七八岁)力气不够,只背了80多斤红薯干。又搭货运火车回来。
经过几天几夜忍饥挨饿的旅程,我们换来粮食回到德州。那是快黑天的时候。我从火车上跳下,只感到渴得难受极了,胸膛里嗓子里都好像着了火。一眼看到不远的工房外有一个大保温桶(应该是铁路工人饮水用的),便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趴在地上,用嘴对着水龙头喝起来。我想那时我的高级神经活动已被一种生存的本能驱赶到一边去了,根本未想这样做对不对。
正喝着,屁股上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爬起来一看,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正怒气冲冲地准备再踢第二脚。我连忙逃走,那人一边追着,一边骂道:“混帐王八蛋!到这里来喝水。这一桶水全让你糟塌了。”
想起来,也是我的不对。怎么可以不讲卫生,嘴对水龙头喝水。再说我当时那狼狈相——破衣烂衫,煤灰满面——人家怎能不讨厌。不就是因为没粮食吃吗?一个人,倘到了几乎饿死渴死的境地,那他还会顾什么脸面,讲什么卫生?
政府和铁路部门对饥民扒火车去换粮食,并不强行阻拦。我与乡亲们在车站扒火车,要先询问火车的方向,铁路上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扒车换粮食的,就指给我们应该上的货车。这也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事。
我也曾到临清买粮食,那时我父亲已调到临清上班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托熟人用汽车运到德州,我再骑自行车驭回村里。
那些年在农村,吃尽了没有粮食吃的苦。真是一言难尽。与乡亲们买粮食的路上,拼命骑行后休息的时候,还有在地里出大力汗流浃背劳动的时候,乡亲们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我:“我们这些人,祖辈就是农民,也就这样了;你这城市里长大的小孩,竟也被打回农村,受这些不是人受的苦……”后面往往是一声叹息。
我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年里,也确实为自己鸣不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入老年以后,这才设身处地地想想农民们。他们一生辛苦劳作,在我们家乡直到如今大多数人生活和医疗保障,还是比较薄弱。我不过在一生中就有那么七年半的时间,在农村里过了一段吃不饱穿不暖出苦力的日子,后来说不上很好,但起码吃喝不愁,生活和医疗有保障。可中国的农民,包括我家乡的村民,当年我和他们一起劳动,几年后我离开了,但他们一直劳作几十年,现在往往还要继续劳动。只要能干得动,就得出力,因为他们那么一点养老钱(大约一二百块钱吧),实在不足以安逸地养老。尤其是怕得病,现在虽然也有医疗保险了,但只是报销一部分。如果得了大病,成千上万的花钱,他们哪里有钱?
说到看病。我在家乡时,人们得了病,小病就扛着,因为即使请村里的赤脚医生看,拿点药,也要几毛钱或一二块钱。对于没有很多收入的农民,花钱看病,也很心疼。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得了病,常常请赤脚医生或乡村的中医大夫看看,抓几副药吃。治不好也就听天由命了。我在家乡几年,没有看到哪位老人晚年病重时,到县城或城市看病、住院或动手术。我说的远,指东去德州人民医院(约15公里),西去县医院(约20公里)。更不要说去大城市看病了。
有些青年人或中年人,没有钱也照样有病得不到好的治疗,早早离世。我的一位表叔,从不到20岁得了肺结核,整天咳嗽吐黄痰。挨到近30岁过世了。我们村里扬水站上操作柴油机的一位乡亲,当时也就40岁左右。在德州医院检查出癌症,把家里养的猪卖了治病。一头猪当时可卖五六十块钱吧。很快花完。没有东西可卖。也就没法继续治,不久就去世了。
赤脚医生的有些治疗方式在城市人看来不可思议。例如给人注射青霉素从来不作皮试。注射用的针头、针管,用完后放到热水里冲洗一下,就给下一个人用。
当然,政府也在努力地培训赤脚医生和接生员。那时是新旧交替。比如接生,我们村里,有人家请没有受到现代医学训练的接生婆接生,也有人请受过西式医学训练的、政府认可的接生员接生。但有一点,也要肯定,那时农村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医生,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态度很好。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有人需要,随叫随到。到了病人家,处理完,到了吃饭时候,病家常常留下医生吃饭。那时医患关系很好,从没听说,病人对医生治疗不满意或试图追究责任。医生受到普遍的尊重和信任。(待续)
荣生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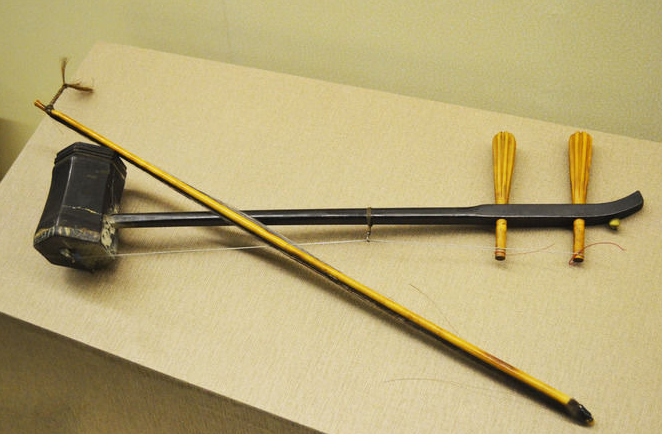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