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美,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己之意)。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也),求矩矱之所同(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匹也),摯皋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呂望之鼓刀兮 (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甯戚之謳歌兮(甯戚,衛人),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飲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也),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恐鷤鴂之先鳴兮(鷤鴂,一名鷶[危鳥],常以春分鳴也。使百草為之不芳。言我恐鷤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
段意:轉求巫咸夕降,亦告我當離開楚君,求明君,索賢臣為同志,共為大化。不但舉出商湯夏禹都與賢臣合兩美、不用媒介,而且舉武丁用傅說、周文王用姜太公、齊桓公用寧戚“三賢”例子爲證。希自己趁年未老,鷤鴂未鳴,助君成化,免使忠直之士受到讒害。很明顯,忠臣悲劇的魅影一直籠罩着他的神魂。
作者:此亦編輯者參酌“淮南資料庫”為混屈原立言,故作波瀾而已。
要點:念楚國 巫咸 知己之意 恐鷤鴂之先鳴
77 念楚國
王注 “心猶豫而狐疑” 句指出,屈原很想聽從靈氛爲他占卜的選擇,即離開楚國; 但心中猶豫狐疑還不想走的原因,是他仍思念挂念痴念楚國;就是他在那裏受夠了讒言誤解排擠陷害因而被長期放逐的楚國,更是其昏君佞臣不把他置之死地而不快的楚國。對如此之楚國,屈原還是如此心心繫念,可閔可欽啊!王逸似乎把屈原之忠於楚國、楚君,置於絕對的高度,越遠越忠,越仙越忠,現在是占卜越靈、越要他遠離,他越不想離。歸根結底,他的忠,遠非對楚國人民之忠,應是對楚國之忠;尤其是對楚君之忠。這樣的忠,漢及其下的專制皇帝們哪能不喜愛啊。
78 巫咸
對這個人物,王逸只注“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可參《莊子·應帝王》“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我們知道殷中宗為殷高宗武丁(約1250至前1192年在位)的父親,離楚國的屈原近千年了,似乎越古越神,“屈原” 對他, 不像對靈氛那樣下命令,而是“懷椒糈而要之”,即獻上香椒精米求他下降人間,來為他卜筮吉凶。 他降下時,場面大得驚人,巫咸在天上頗有權威吧(反正作者和編輯者對他備極尊崇),他竟然率領百神遮天蔽日而下;而且,還有“九疑繽其並迎”(迎巫咸,更迎屈原)。可見屈原面子也很大。據王注,這大概應是因舜的影響,“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己之意”。大概通過“陳詞重華”,舜成了他的知己了。
79 知己之意
舜竟然以這種形式對屈原表“知己”之意。從前文第十四段我們已看到屈原長篇大論向舜陳詞求教,舜卻未置一詞,看不出對他多麽知己。《漢書·楊雄傳》載其《反離騷》曰“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句下張晏注曰“舜聖,卒避父害以全身,資於事父以事君,恐不與屈原為黨與。”意思是舜很聖明,終於避開其父對他的陷害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根據人臣要如奉事父親一樣奉事君王的道理,舜恐怕不會引屈原為同黨同志—也至少顯示舜不大喜歡和屈原説話。在《遠遊》中屈原卻自比舜、並以舜得不到堯的知遇(繼位)而自傷!現在,王注公然說,舜使九疑之神紛紛都來接近我,來表達他的知己之意,其意不知所從何來,當然任王逸等杜撰。然而向舜陳詞、為舜知己,以舜自喻,出現在不同的選段中,各表其意,當然不必連貫或統一。但我們正可從中看出,自劉向至王逸編輯們處理的同一聖帝對屈態度的不同,可見聖君都是很隨意的,否則怎成聖君呢。
更奇怪的是,屈原現在跑到什麽地方了、九疑之神才忽然都來接近他?從南濟江湘地近九疑而向舜陳詞,到朝發蒼梧(離開舜)、東極飲馬、 高丘無女(在昆侖),以下求宓妃、求簡狄、求二姚,問靈氛,直到本段求巫咸,我們讀不出任何關於九疑的地點暗示,便忽然讀到九疑山的衆神都來迎接他。好像他在任何地方九疑衆神都可隨時迎迓,這就不可思議了。是不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與任何神祗互動?這種毫無預示的文思飛躍,如此令人追之而不及, 難道因爲是神仙思路嗎?確切地說,應該是求仙者的冥想、幻想而已,所以舜何時開始對他有“知己之意”雖無從説起也是可以理解的。 造成這種突兀不接的另一原因,是編輯安排不同段落時造成的文脈斷裂。幻想的雲游描寫與頗不融洽的段落隨機組合拼合,造成以《離騷》爲代表的《楚辭》文字往往突兀不接,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在這種情況下 “告余吉故” 就是“百神告我當去(即應當離開楚君)”,當然毫不奇怪,因爲編輯早就説了,屈原能“役使百神”,讓他們迎合自己的意旨做這做那,常常竟是不受時間和地點限制的,或稱不受尋常邏輯限制的。
80 恐鷤鴂之先鳴
鷤鴂,也寫作鵜鴂,就是杜鵑、杜宇(蜀王所化,典出《史記·蜀王本紀》或晋張華注引漢李膺《蜀志》),後世也叫子歸、子規,據説每年春分(或謂秋分)前後鳴叫,叫聲凄厲悲慘,叫得好像鳥喙都紅了(被稱爲杜鵑啼血)。其鳴之後,春花就開始凋謝了。王逸如果只認爲原作者的意思是珍惜青春年華,要及時努力,應無問題。但他偏要繼續把比喻的内容推演下去:“言我恐鷤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這就不但把 “華英摧落” 歸罪於本來只是報春之歸去的鷤鴂,而且把“華英摧落”所比喻的“忠直之士被罪過”也當成了鷤鴂造成的惡果,以“鷤鴂先春分鳴”“喻讒言先至”,簡直差不多把“鷤鴂鳴” 比喻成讒言了。王逸爲何如此落筆而冤枉鷤鴂?當然是爲了强調所謂“忠臣悲劇”。
第二十一段 瓊佩偃蹇 芳草蕭艾
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眾盛貌),眾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眾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惟此黨人之不亮兮(信,亮也),恐嫉妒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妒我正直,欲必折挫而敗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余以蘭為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棄也),苟得引乎眾芳(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眾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椒專佞以慢慆兮(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樧又欲充其佩幃(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
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也),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蘺(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眾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眾芳,此誠可貴,茲不遭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歇也)。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誠難虧歇,至今猶未已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
段意:自言多佩瓊玉、富有盛德,而衆人掩蔽之。黨眾不尚忠信,必欲折挫我的正直。時俗混濁變化,我哪可再耽留下去。如今君子變為小人,忠信更成佞偽。明智之士,皆佯愚避禍。此皆君王不好修、不用忠之害。我本以蘭可依恃,不料竟也毫無誠信之實;放棄美德,隨從諂佞,只想居領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又椒樧也專佞淫慢,欲填滿他(君王)的香囊,同時想援引當面服從而不賢的人,使他們居親近之位。子蘭子椒自謀權位,何賢之能敬。 蘭椒猶如此,眾莫不效之而諂諛變節。自己内美雖可貴,只能棄之而忍受苦難。 自己所行芬芳(忠貞)雖不見用, 還要執而守之,以自娛樂而求同志。願及年德方盛,周流四方, 觀察合適的“上”(君)和“下”(臣),以便自己安身立命。
作者:此亦編輯者參酌“淮南資料庫”而成,其中多爲劉正則言者。
要點:美德偃蹇 蘭芷荃蕙 蘭椒 兹佩可貴 所行芬芳 求女 同志
81 美德偃蹇
原文“何瓊佩之偃蹇兮”,大致應解作“我的瓊玉之佩何等高揚(高揚,或如王解作眾盛),王卻解作“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等於把“瓊佩之偃蹇”直接意譯成“美德偃蹇”,則不管如何解“偃蹇”,“瓊佩”實際上被當成了“美德”。“瓊佩”比喻或象徵美德,可矣;直接以“瓊佩”代美德,把喻體放在本體之前,又成了前文所指出的“忠信A”,這種美德實質上是做給人看的、人工合成的美德,當然是假的美德,是中看不中用的美德。
82 蘭芷荃蕙 蘭椒
王逸注“蘭芷變而不芳兮”二句為“言蘭芷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這是一般性地說昔日的芳草(蘭芷荃蕙)都變成了蕭艾, 忠直之士也變成了讒佞之輩。這當然是因“上”之不好修所致。
接下去,香草居然開始比喻(代表)具體的個人。“余以蘭為可恃兮”二句,依王注,我本來以爲(子)蘭可以依靠,不料他(它)毫無誠實、空顯得頗有又長又大的氣象;抛棄了美好正直之性,隨從阿諛奉承的風俗,只想登上可以引薦賢人的地位,卻毫無進賢之心。可見,蘭花一變而成了楚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果有此人乎),從起政來。
“椒專佞以慢慆兮”句,專佞,應是專事諂諛;慢慆,謂驕慢過火;根據王注,“椒”又被説成喻楚大夫子椒,子蘭子椒,無獨有偶,已令人稱奇。 “樧又欲充其佩幃”句,王注曰“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把似椒而非椒的樧,比似賢而非賢的子椒,讀來總覺爽然若失。細思二句,則是以蘭花喻子蘭,以椒樧二花喻子椒,豈有以一花喻A,同時以二花喻B之邏輯乎?則A、B二喻,皆無根之言也。
而這個樧,居然 “又欲充其佩幃”,意即又想充滿王的(其=他的=王的)“盛香之囊”,王注“以喻親近”。“充其佩幃”中的“其“字,即指楚懷王的,能“充懷王之香囊”,自然親近。王逸大概還怕讀者不明白其用心,又補充說“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意思大略是: 屈原說子椒作爲作爲楚大夫,其“椒”處在蘭芷香草之間,推行他的讒上驕下之志 ,又想引薦那些當面阿諛從命的同類,讓他們都處於王的親近位置,毫無為國擔憂之意。--都是指責備他們的。可見,樧不但欲以自身“充其佩幃”,還想“援引面從不賢之類”,即與這樣一群人結成一夥,來完成他的政治結黨事業。王逸不但比蘭花為子蘭,而且比椒花為子椒;況且把樧一起合并入椒來比子椒,甚至在注解中進一步把所謂子椒薦引的一群馬屁精都解釋成充斥香囊的“樧”。王逸確實善於不動聲色地利用極度誇張來表達他的真意,通過這種形式上看似吹捧或贊揚的描寫,可以看出他對所謂子蘭子椒的存在表現了一種嘲弄性的否定。其實,連楚屈原也不過是漢朝政治運作產生的假楚喻漢的虛幻存在,子蘭子椒等更是可有可無的影子人物,或充其量為跑龍套的群衆演員。
83 兹佩可貴 所行芬芳
“惟茲佩之可貴兮”二句說,我這身芳香的佩飾猶如我的忠誠一樣可貴,但我因不遇明君不得不放棄這種至美而落難如此。從比喻的角度言,仍然是省去本體(所謂内行忠正、即忠誠)而只提喻體(兹佩),這樣能强調本體本身嗎? 下二句接言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 王注曰“言己所行芬芳,誠難虧歇,至今猶未已也”,意謂我所行的道德,其芬芳至今未已;王注直接以“芬芳” 代替道德。這也正是我們在前文多次次提到的“忠誠A” 的同類表達,也是以喻體直接代替了本體。也猶如說光緒的蘋果像其珍妃的臉,是贊揚蘋果,而不是贊揚珍妃的臉。 再説一遍,在《楚辭》中,這種故意的本末倒置不是偶然的,而是始終一貫的。
84 求女 同志
“和調度以自娛兮”二句,説要調整自己、自娛一下,似在繼續浮游而處於猶豫未決狀態;繼續求女,是假裝求所謂“同志”。“同志”一詞不知是否為王逸們的發明。反正屈原沒有同志。假“屈原”(不存在)不可能有,連他的歷代粉絲們(不管是否知道他的虛無身份)也不能成為他的同志。真屈原獨步千古,在當時乃至後世即使發現他贊揚他的人也幾乎無人夠得上成爲他的同志。至於自稱“及余飾之方壯兮”,按照《楚辭》常見的修辭習慣,這裏的“飾”,由外在的佩飾、風度,年齡、到内在的德藝、意氣、智術,都可包含在内:然其基本内容應是“趁自己方在少壯之年”(年富力强修德高能)。我們由此仍然推定此處的發言者是死時剛滿四十歲的蓼太子(前163-前122)。而求女與求同志, 合在一起便是求“女同志”,在前文“求女”論題中已提到,最多是原作者通過房中之術修煉求仙的、較般配而情投意合的性伴侶。
第二十二段 邅道崑崙, 神魂高逝
本段達到全文高潮,可分三個部分,其意綜括為:從靈氛占而遠逝自疏,周流諸天四極,在仙遊中似逼近自己的政治理想。爲方便,今分A、B、C三個,段下之各論之。
作者:都是被編輯過的劉正則。
A 遠逝自疏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羞,脯也),精瓊爢以為粻(精,鑿也。爢,屑也。粻,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粻,飲食香絜,冀以延年也)。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
段意:乃從靈氛占、擇吉日、辭君而行。携糧食、整車馬,遠逝自疏。
要點:去君遠行 瓊枝瓊爢 德似龍玉 己德似龍
85 去君遠行
觀《離騷》全文,大約在敘及“陳詞重華“之前,主人公已被放逐而離開“君”;現在卻又“將去君而遠行”,好像他還沒離開君一樣。這該如何解釋呢?第一種可能, 大可認爲那楚屈原的心以前真的從未離開過“君”,這次離開是第一次。第二種可能,不同的編輯或注解者在處理各種細節上可能不盡相同,而最其後的王逸亦未能彌補和消滅全部瑕疵而留下種種可疑可議模糊處乃至漏洞,而聽任讀者自解了。第三種可能,文中主人公所謂的被放逐,只是一種設詞,是被君王疏遠、遠離權力中心、不復在位這種情狀的比喻之詞。 所以是否“去君”,可任作者乃至編輯者隨便説。下文“路脩遠以周流” 的王注亦云“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但假屈原任擺佈而已,能怎樣離楚遠行;考慮到整部《楚辭》中“假楚喻漢” 的暗喻手段, 真屈原劉正則自也未離開過漢之疆土。去楚遠行,只是現實壓迫下理想或幻想的浮現而已,所以只是“設”(假設),是虛擬語氣下的敘事。
86 瓊枝瓊爢
“折瓊枝以為羞兮”二句,王注云 “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粻,飲食香絜,冀以延年也”。意思是出行之前,折斷瓊玉之枝做成乾肉,細鑿玉屑當糧食,服食這些美味潔净的東西,希望用這種方式延長壽命。這其實等於宣佈了原作者通過服食以求神仙的行徑,和漢魏間的方道之士的服食求仙後先相對照。其所服食者,不外植物或礦物,植物如菖蒲、靈芝,礦物如石鐘乳、硫磺、丹砂等;加上房中之術、導引之術、冥想之術、飛行之術(后二者或認爲即現代的氣功),凑成古人求長生的幾乎全部法門,當然也表現在淮南子神仙家的試驗、實踐中,表現在《楚辭》系統的作者敘事中。
87 德似龍玉 己德如龍
“為余駕飛龍兮” 二句王注“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這裏提到乘駕龍、象,分別表“德似龍玉”中之“龍”與 “玉”。其中所謂明知之獸或神智之獸的“龍”,應在秦漢之間最終成爲帝王專屬的象徵性名詞或形容詞(秦始皇稱祖龍、劉邦有斬白蛇起義的傳説,白蛇似龍不如龍)。“象玉之車”,大概是有象牙為文飾的車;《周禮》載“王車五路”,指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雖未確知起於何時,也指古代帝王車駕。這兩句其實是自負帝王之體、有聖帝卓特之質、絕遠之能,可惜的是古今讀者莫識—當世不知,後世至今也似不欲知也。下文 “載雲旗之委移”王注 “言己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這裏說屈原自認爲“己德如龍”,能“制御八方”“德如雲雨”,也更分明表達作者有等同帝王的、平治天下的文韜武略、胸襟氣魄乃至政治理想。這與本文第一段的“修能”之王逸注不謀而合,或者説是自然一致。
B 周流諸天
“邅吾道夫崑崙兮”(邅,轉也。楚人名轉為邅),路脩遠以周流(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雲霓之晻藹兮(揚,披也。晻譪,蓊鬱陰貌)。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蓊鬱,排群佞之黨群,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夕余至乎西極(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乘旂兮(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高翱翔之翼翼(翼翼,和貌也。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乘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段意:轉道昆侖周流天下。揚雲霓鳴玉鸞,朝發天津夕至西極。為懷有德,彩鳳來儀。
要點:邅道崑崙 周流天下以求同志 天津西極 鳳凰來儀
88 邅道崑崙
“邅吾道夫崑崙兮” 不僅是轉道昆侖,更應是最終不得不決定取道昆侖,希望達到求仙成功。前文“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其中蒼梧是舜葬處。而王逸注曰 “縣圃,神山。《淮南子》曰 ‘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乃維天’”,其中“乃維天”是帶强調意味的肯定判斷,即“就是天”的意思。縣圃是昆侖山中的神山,可見作者足跡已到了昆侖,即“天” 界。本段下文 “揚雲霓之晻藹兮” 二句王注“言從崑崙將遂升天”,卻表明昆侖是所從升天之處,尚不在天界。這算是個小小異文吧,入天之門,其名本來就是編造的。在全是斷片的幻想連綴中,無論怎樣精密補綴彌合,有諸如此類的小疵是難免的。以下《淮南子·原道訓》應是原文及王注所本。“經紀山川,倒騰昆侖,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注“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宫門也”。又《淮南子·地形訓》云“傾宫、旋室、縣圃、凉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又云:“昆倫之丘,或上倍之,是謂凉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縣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這一段前文引過,今不必重複而在再引,是爲了强調和不煩讀者翻檢)原來昆侖閶闔包括縣圃等五個升天門戶;而稱“天門”者是“上帝所居紫微宫門也”。記錄神話之詳細,簡直似地理消息。
89 周流天下,以求同志
王注解釋“邅吾道”句為 “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好像爲了到達昆侖,他已經過雲天萬里而“周流天下”、即找遍天下能找的地方,也找不到同志,才去直通天上的昆侖山去找。在昆侖山好像也沒有找到。所謂求同志者,乃是尋求真正理解并且支持他成仙的人(包括前文所謂女同志,應也包括讀者)。王逸大概自認是《離騷》作者合格的“同志”,他的《章句》之曲筆雖然千折百回,卻能真的直追正則靈均之文心。所以,為成劉正則之同志,我們首先要努力正確理解王逸。
對於設定的楚假屈原(查無此人)而言,編輯者當然很難爲他找到一個和他一樣盡愚忠於楚懷的同志,而只能找到極多自以爲理解卻並不真理解他的粉絲。對漢真屈原而言,王逸們(即編輯者們)除不得不作表面文章來應假屈原之景外,堪稱對他心馳神往、爲他費盡心機、曲盡其幽、惜墨如金地保留了高度肯定和贊頌的筆墨,也很想努力爲他找當時乃至後世的同志。但與此同時編輯者們還有一個極其困難的任務,他們編輯的《楚辭》所必須表白的最隱秘最可貴最真實的消息,必須讓專制暴君本人以及受他權力籠罩和洗腦的文人們讀不懂而基本上看不出來。這個任務雖然大致完成了,卻同時也造成了蒙蔽絕大多數古今讀者,使他們對《楚辭》茫昧而不知主旨的結果。其可悲在於,我們的民族被令人腦死的忠君文化毒化和蠱惑了幾千年,居然造成絕大多數讀者,包括很多所謂專家學者,竟然不能看懂《楚辭》的真話,而只是大肆吹捧他不得不説的假話—這樣的惡果!所以至今沒有人能成爲真屈原的同志。而《章句》對於楚假屈原忠君的大肆渲染和揄揚(儘管有恰到好處的描述),卻推波助瀾,形成忠君文化最燦爛的毒花乃至毒果。
筆者對靈均珍秘稍有所解,亦不敢妄稱其同志。願與所有求真知者共勉,直到水落盡石全出之時。如此,方可告慰靈均、告慰叔師啊,嗚呼靈均,魂兮歸來!嗚呼叔師,靈兮歸來!至此,爲了研究“屈原”, 我們更應研究對於屈原的研究,在“周流天下,以求同志” 的廣度和深度上,加上時間的維度,就是“周流古今天下,以求同志”。
90 天津西極
“朝發軔於天津”句王注:“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 “夕余至乎西極”句王注“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天津,就是天河(銀漢)的渡口(這個神奇的名字至今被用於通向京城的大港口城市,真有意思);早晨啓程於萬物所生的東津(應是東極),晚上到了萬物所成的西極,動輒依照陰陽之道規劃自己的行爲,而且極其迅疾—王逸這樣解,是爲了表明屈原有經緯主宰天下的局度。王解大抵不錯,但似乎有點小毛病,錯在說天津是“東極箕斗之間”的漢津。根據《淮南子·天文訓》“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則 “箕斗之間” 的“漢津” 不當在東極,而在房、心、尾所居的變天之星野。王注爲什麽有此偏差,或此是否算偏差,不得而知。
91 鳳凰來儀
“鳳皇翼其乘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二句王注曰 “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乘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其實《尚書·益稷》早有解釋“《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孔傳﹕"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又《禮記正義》卷三十八《樂記》第十九“《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舊說其樂奏到高潮,則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莫不歡忭鼓舞、擁戴聖君的善政,即此處“嘉忠正”也;嘉許中正之臣,為假屈原而寫,是掩飾性浮言,而“懷有德”,是擁護有德之君,其實為劉正則私下自詡也。
C 簫韶九成
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也),騰眾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眾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車,遠莫能及)。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己使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齊玉軑而並馳(軑,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從己者眾,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之委移(言己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也。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是也)。聊假日以媮樂(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
段意:梁津蛟龍、詔命西皇。駕八龍、載雲旗、抑志弭節、元神高馳,奏九歌, 舞大韶。假日媮樂。
要點:動以清潔自洒飾 麾蛟龍詔西皇 過不周左轉 奏九歌而舞韶
92 動以清潔自洒飾
行流沙、遵赤水,王逸對此二句除可做一點地理上接近昆侖的位置解釋,本別無可言。但他還是要提醒讀者這位屈原 “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即雖在遠方奔波,還是常常爲了道德清潔洒洗自己、修飾自己的儀容;原文只提到 “遵(循)赤水” 而游戲前進,王注偏要强調原文并未提到的沐浴、游泳,而且連“行流沙”也捎帶加以强調,説自己所行雖遠,卻不能因爲離開君王遠,就不洒洗修飾自己的儀容(要堅持和提高自己道德修養、忠君懷抱)。可見,即使“跑”到天邊去,還要發其“越遠越忠”之鳴,而且還要發給後人看。這除了可能是編輯者在細節上爲他設定的道德傑構還能是什麽呢?
93麾蛟龍詔西皇
王逸注“麾蛟龍、詔西皇”此二句,“乃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云云,應也是爲了顯示為此言者之人君的擔當和氣度。自秦始皇被稱祖龍(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之後,“龍” 逐漸取得或成爲帝王專用語的資格;能夠 “麾蛟龍”已自非凡,況乎“詔西帝”。
以下專說“詔西帝”之“詔”字。筆者本來望文生義,以爲“詔”字即“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詔”,是皇帝向下傳達其意旨而專用的詞;讀到王逸注曰“詔,告也”,卻覺得 “詔” 可能本來只是中性的、告訴的意思,不分上下等級。但是查到《説文解字》等一堆工具書,總括各種説法,結論居然證明上言“望文”所生之義是正確的。以下幾段網上查到的材料可証。
王念孫《廣雅疏証》“詔者,《獨斷》云:天子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詔,誥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命為‘制’、令為‘詔’。”裴駰《史記集解》引蔡邕:“詔,詔書。”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此字(詔)《說文》不錄。徐鏇補入。從言,召聲。誥也。按上告下之義,古用 '誥’,秦復造 '詔’當之。”鈕樹玉《說文新附考》“《史記·始皇本紀》廿六年:'丞相绾等與博士議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見秦刻石),天子自稱曰朕。’則詔字當始于此。”“先秦古書本無詔字矣”(在先秦“詔”僅見于秦文字)。所以,《離騷》“詔” 字用法,可看作該文是作於秦之後、即漢代的一個小小的證據。
“詔西皇使涉予”,就是以尊于西皇的身份詔告西皇,命他把自己渡過(西海)去。對比上句 “麾蛟龍使梁津”王注“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動詞 “麾”乃揮手(指揮)之意;梁,橋梁,津,渡口;今二字一起用作動詞,大致是命蛟龍用其身體架橋通過或者直接飛越西海而超越、替代橋梁的作用,就算完成“梁津”任務了。但這又似與“詔西皇使涉予”意思相重:既指揮蛟龍搭橋成津過西海,又詔告西皇渡他過西海。原文這樣重複設計,應只是爲了炫示作者的揮手令百神的局度(帝王風度)。但這種重複的强調構成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誇張:若蛟龍和西皇同時遵命,都來助屈原涉渡西海,這將會形成一種怎樣的(混亂)局面啊。
其實以上令西皇出場,同時暗涉另一個角色“東帝”。《淮南子天文訓》 “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徙嚴道,道死於雍”。《淮南洪烈解》“歸國,為黃屋左纛,稱東帝”。賈誼《新書·治安策》及《漢書賈誼傳》“今或親弟謀為東帝”。這個“東帝”就是《離騷》首句第一字“帝”之所指,亦劉邦劉長劉安劉正則這個洪卓家譜中之第二人也(又頗疑“東帝”亦暗指《九歌》中之東君甚或東皇太一)。可見所謂西皇者,應指與東帝相對的漢帝,而不只是表面上的古聖帝少昊。實際上,西皇若指少昊,根據《帝繋》,少昊乃所謂屈原祖先顓頊之叔、即顓頊的前任聖帝,屈原當無資格這樣詔告他做這做那;而若指漢皇,即使“詔告”意只是平等的告知,也暗寓逆天之罪。看來“屈原”之求仙而“役使百神”,是他招致殺身之禍的重要原因。即使只役使神仙世界的風伯雨師,也早超過時君的忍受極限。所以司馬相如(似應詔寫)的《大人賦》中有“刑風伯,誅雨師”言,其意在于,不但悍然用氣勢而且公然用殺氣—來壓倒“屈原”(劉正則)的 “役使百神”。
錢鍾書先生引此稱為“前後失照”之一例,他舉了《離騷》“麾蛟龍詔西皇”二之前幾句,直引到本句(《管錐编-楚辭洪興祖補注》第二則《離騷》六:“如本篇云‘為余駕飛龍兮,雜瑶象以為車。……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乃飛龍為駕,鳳皇承旌,有若《九歌·大司命》所謂‘乘龍兮車轔轔,高馳兮冲天’,乃竟能飛度流沙赤水而有待于津梁耶? 飛龍為駕,鳳皇承旗,有若《九歌大司命》所謂“乘隆兮駕雲,高馳兮冲天”,有翼能飛之龍詎不如無翼之蛟龍耶? ”
很顯然,錢先生以爲,屈原乘龍既能飛度流沙赤水,當然應能飛越西海而不需要梁津。還認爲要渡西海,“麾(無翼之)蛟龍使梁津”句中的 “蛟龍”,遠不如“有翼能飛之龍”(飛龍)更爲勝任,竟考究龍之有翼與否,那麽有翼之飛龍直接飛過去便可, 還要無翼之蛟龍架什麽橋!這種讀法雖似有理,但直接以現代關於飛龍和蛟龍嚴密的動物學知識來推斷屈原冥想或幻想中的流沙、西海之飛行,好像太過認真了。
我們也“認真”一下:“飛度流沙赤水”的“交通方式”,應見於“路脩遠以多艱兮,騰眾車使徑待”二句。依王注“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尋常人力所能攀越。故令眾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車,遠莫能及”;意思是,因爲昆侖路險,自己所乘車速度又快,衆從車都遠遠趕不上,所以下令衆車,讓他們在“邪徑”(當指大道之側便捷小路所通的停車地)上等待自己超過他們(再前進)。由此可知,行流沙,只是在流沙上行進,遵赤水,也是沿循赤水行進并且游戲;而且這一段游歷是與衆人一樣,乃乘車而行。不過他所乘車乃是衆車遠不能追及的快車,至於其車是“蛟龍”或“飛龍” 所駕(或者美稱其馬為龍),真是不可料及也無法考證之事。作者文思變化,經常令讀者目不暇接,神不暇迎,往往不可以尋常邏輯解之;而且所謂周天之游經常是以意行之,是作者任意取興,而編輯者則信手拈來、隨機拼合的一些斷片“視頻”而已。而且,即使真能將詩人之意識流用視頻表達,前後斷裂、失照之處所在多有也是必然的。
從根本上講,編輯者是將不同作者的相關段落、或同一作者不同時間寫的段落聯綴拼合,稍加改動性潤色,救首救尾,如拼圖一樣構成一個頗有整體規模之全文的。其文似乎高不可攀、深不可測,又有無數先儒大賢異代同聲、爲之高唱贊歌,令人不敢輕易議論。其實《楚辭》語言,因爲是很多片段的連綴,又調子過高,多有繁冗重複及文思割裂之處,王逸雖常欲彌縫缺漏,而力所不能全及也。所以留下很多問題,很多暗示,有待好奇而憧憬的欣賞,有待忽略或有待揭示,當然也有待解決。
在此還應特別提出的是,班彪《覽海賦》提出所謂“命韓眾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的要務, 竟幾乎未曾引起任何學術注意,談何付諸研究實踐。實也令人嘆爲觀止!我認爲,研究《楚辭》而未讀過《覽海賦》,是談不上能校正任何《楚辭》文字、 也不能解決大多數有關《楚辭》篇章及其作者的問題的。“神篇靈章”需要在王逸所顯示、所藏匿的内容基礎上,仔細勘察、重新講解,有所發現和發明,糾正王逸之後至今的研究者甚至連王逸深心提供的事實都加以忽略的傾向。這是任何楚辭學者、乃至中國文化學者必須面對的大問題。也是衡量他們的研究有沒有、或有多少文化價值的主要尺度。
最後,綜以上分析,“麾蛟龍” 二句,似應移置於下文“指西海以爲期” 二句之前,這樣既不影響周圍群句之連貫性,也加强了這四句的意義銜接。這個語序問題也許非王逸之過,而是兩千年來版本輾轉翻印造成的。
94 路不周左轉
取路不周山而向左行,到底轉至什麽方向?不周山既在昆侖山西北,從楚國奔赴不周則應從東、南來而朝向或西或北,然後再左行就朝南或朝西了。但王注 “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意思似說不周山本身就坐落在“道不合於俗”的方向上,不講什麽南北東西了!到了不周山而“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向左轉竟成了君王向行爲左乖、不合理、心地卑鄙的方向轉變和滑落,自然和自己不是同志。怪不得“屈原”一直找不到同志,他希望所寄的君就十分固執地不把他當同志。過不周而左轉之後,據説就“使語衆車,俱會西海之上”了。把 “過不周” 解成“道不合於俗”、“左轉” 解成“君行左乖”,此類怪解顯然是王逸很方便地隨文曲解、故意地望文生義,不但不顧地理上的方向,而且總要不管場合、不厭其煩地把屈原的忠誠和忠臣悲劇反復示人。連在乘龍駕雲的路上也如此曲解—簡直要故意誘其讀者迷失方向。
95從己者眾,皆有玉德
“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齊玉軑而並馳(軑,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從己者眾,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
細琢磨原句和王注的意思:屯聚和陳列我的從車,前後就有千乘之多;衆車都以玉做車轄,在我左右馳騁;而且這些跟從我的衆人都有玉德,真適合輔佐千乘之君(我)啊。這話表面好像如實陳述自己是千乘之君(不攀比萬乘),但細看他的從車千乘,竟“皆有玉德”,則千乘從者皆為君子賢人也。延攬賢臣之聖主,得幾個甚至一個卓越的賢人君子,已足致治,今得千乘皆賢,其聲勢之浩大、德容之尊偉,遠過聖君的賢德臣僚矣。千乘從賢尚有玉德,其本人更應是玉德玉質玉體了。
蓋君子比德于玉,有德似玉,有玉表德,乃有玉澤之質,美玉之體也。此人·非帝王級別而何?《禮記聘義》載孔子論玉十一德(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长,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又許慎《説文解字》論玉五德 “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潤澤以温,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原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潔之方也”。《楚辭》編輯者在多種場合强調屈原玉德,心中當然有孔子論玉十一德在,有時幾乎直接以“玉”代“屈原”(劉正則)本人。
前文有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二句,何爲昭質?王注“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無有虧歇而已”—特別提出自己“內有玉澤之質”即“玉堅而有潤澤”,實自謂其德質如玉,亦超卓而自然,顯出聖者真相。又“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岂珵美之能當”二句,王注“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眾草尚不能别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也是自比美玉。鑒於以玉頌美屈原例子之多,稱之爲金相玉質自不爲過,以玉代之恐也不爲過。 前引《九思·遭厄》中,“悼屈子兮遭厄,沉玉躬兮湘汨。 何楚國兮難化,迄乎今兮不易。”—則直接稱屈子之身體為“玉躬”也。
由《楚辭》中這個重要的竟有人當時遭滅名、後世因而加代名的例子,我們可再猜測一下或許還有可能的遇滅名之難者。例如雷被伍被毛被,這些淮南王門客們,爲甚麽都叫被?在淮南重要門客這樣小的範圍内重名幾率如此之高,令人不得不起疑:被,就是被遮蓋掉,是否這是滅名不滅姓的半滅名之懲罰的結果呢?由此聯想到後世對屈原“金相玉質”的稱頌而想到宋玉,這宋玉似真名、又似化名, 爲什麽呢?《漢書·嚴助傳》“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書言事,聞之”云云所言“中大夫玉”竟然不提其姓,其人似是淮南王國官員,不知何故網漏吞舟之魚,沒有被殺(刪)掉。但《漢書》僅有此四字提到他、而別的相關正史記載似乎已全刪掉而把他湮沒了。那麽這個(宋)玉也很隱晦地藏在歷史夾縫中,我們是不是可以猜測這個名字暗藏着“頌揚屈子(劉正則)”之意?至於唐勒,漢宗唐堯,而以唐字代堯字,故唐即漢也;唐勒反言就是勒漢,猶勒馬停繮一樣,以強力諫阻挽回那“天政急”(皇帝大開殺戒殺群臣)而趨滅的頹勢。又,璟, 景也,景慕也,瑳,本意玉色鮮白;故此名或帶貴玉而尊師之意?這些聯想不算研究成果,可以用於噴飯。
96 奏九歌而舞韶
“奏九歌而舞韶兮”二句,王注“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如王注,九歌,是禹時音樂,韶,是舜時音樂,二者都是聖君臨天下時的音樂或治世之聲。故“奏九歌而舞韶兮”不單是奏聖君之樂,而且標志行聖君之政。此處說凴自己的德高智明,應該(輔佐舜禹)達成天下太平,但是自己卻不遇其時,所以他只能在幻想的四荒游歷之中勉强度日,安慰自己,聊得一時之想象的滿足,“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前文已見,屈原多次自詡一代龍象,此處沒有直接點出以舜自喻,而是稍作迴旋遮護。
但對比《遠遊》以下二句“張《咸池》奏《承雲》兮, 二女御《九韶》歌”及王注:“《咸池》,堯樂也。《承雲》即《雲門》,黃帝樂也。…《韶》,舜樂名也。美堯二女,助成化也。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則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於是遂禪以位,升為天子。乃作《韶》樂,鐘鼓鏗鏘,九奏乃成。屈原自傷,不值於堯,而遭濁世,見斥逐也)。—這就是直接自傷不能如舜之“值於堯”而被薦舉了。其實,《離騷》乃至《楚辭》全文中觸及“屈原”的帝王品位少説也有十多處文字,與此同時,也許可理解成人爲强加的忠臣佩飾嗎?鑒定這種文字,多費點斟酌是絕對必要的。
第二十三段 僕馬情懷 彭咸為儀
陟升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
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又何懷乎故都!言眾人無有知己,己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段意:在空中飛騰而臨睨舊鄉, 乃僕馬同悲,踟躕不前。國人莫我知,還是投水吧。
作者:王逸等編輯《楚辭》而爲此結尾
要點:僕馬情懷 《離騷》結尾 從彭咸看漢儒的杜撰
97 僕馬情懷
“僕夫悲余馬懷兮” 二句説到自己不但僕人悲傷、馬兒也憂愁不已、彎著身子不肯前進。又重複説,“屈原設去時離俗(假設背離時俗),周天匝地(環天繞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在天上遠望看見楚國、不但馬夫悲傷,連我的馬也想回歸而盤曲不前)。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這真是不失其畢生終極的志向,用言詞展現自己,用道義映照自己的高尚内心)。這個光輝形象的構成, 其實借鑒了《詩經·周南·卷耳》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詩》中征人、主人公離家奔波而悲思其婦,其悲不但感動得其僕都要病了,而且擴散感動得他的馬兒也走不動了。這當然是悲情的輻射性誇張,可稱之爲“僕馬情懷”,不知何故,很少研究者願意指出此處《楚辭》對於《詩經》的繼承和采用。又,這個“僕馬情懷”也見於《遠遊》近結尾處。
98《離騷》結尾
《漢書·賈誼傳》曰 “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與此處不同。這是極其重要的不同,竟然把屈原投水的關鍵情節漠不關心地刪掉了—這是極其粗心,還是極其細心?讀者可以自便,或自辨吧。這個細節乃至擴大的故事情節,在《楚辭》各篇中確實被神奇地描寫、被反復地表述、被生動地刻畫,被嚴密地定義了多少次,卻仍然不清不楚、可疑可議。我們討論過的《招隱士·敘》中“身沈沒”三個字雙關的表達可謂一字萬金:一是投水而身體沉沒,二是被殺、被滅名而身份沉沒,相信讀者能擇善而從,擇真而從。投水而死是假屈原的故事,被重複最多并不該成爲真理,因爲它反而是謊言,即使是藝術的謊言仍是謊言;謊言重複多次就可以變成真理, 這是專事洗腦的統治者及其幫凶幫閑們相信的邏輯。殺其人而滅其名則是暴君的絕招,也是維護暴君繼續頂戴聖君冠冕的頂級國家機密。這個絕招,使多少本來相信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儒士因恐懼滅名毀名而向暴政屈膝,又使多少被暴君暴政洗腦的無辜臣民以堆積如山的尸體喋血沙場被暴君勉强賞賜一個英雄的名譽!這個絕招,使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發現那至今沾滿鮮血的英雄之名、字!謝謝王逸,向他致敬吧。
99 從彭咸看漢儒杜撰,見附錄8
牟怀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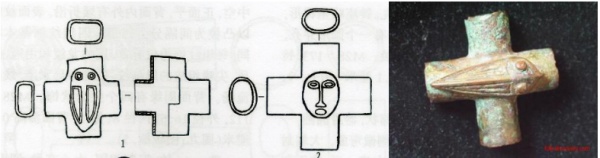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