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8年,我母亲十七岁,4月5日一大早,她跟着出伕的队伍,从高密县呼家庄乡河新庄村往褚家王吴村走,说是去开挖王吴水库。两个村庄的直线距离八十多里,一天走到。我母亲扛着铲土的铁锨,还挎着一个荆条编的提篮,篮子里塞一床窄、短、薄的被子,被里裹着一个搪瓷缸子,搪瓷缸里塞着擦脸毛巾和吃饭的一双筷子。她的前后左右是本村往前赶路的队伍,有牛,有驴,还有一头骡子,最多的是人。男人推着小车,胶轮的,小车左右捆绑着两个条编长篓,篓里放着数把沉重的洋镐,即十字镐,还有几把铁镢,大的就叫大镢,小的则叫小大镢,不叫小镢。开挖水库小大镢没用,所以没带。有一辆手推车专门装着牲口套:口肩、夹杠、拉杠、撇绳、搭腰等,满当当两篓子。
在工地,除了吃饭睡觉,我母亲说都在挖土、运土。挖土的活轻,女人干。运土的活重,男人干。看上去工地上都是光膀子的男劳力。牲口拉着装满土石的小车爬坡,那活可不轻省。人拉车容易受伤,上高坡、陡坡人力玩不转,只有牲口行,都累垮了,人还能轮着喘口气,牲口得连轴转,牛没空反刍,直吐白沫,翻眼珠。后边二十多天的时候,人也受不了了,男人的肩膀、脖子被襻喇出了血,所有人都两手血泡,破了旧的,又磨出新的。再是吃不好,睡不好,吃棒子面、地瓜面窝窝头,咸菜都没有,还吃不饱。睡觉没地方,亏了天不冷,露天地,树底下,扑拉扑拉躺上,盖上破被闭上眼,还别说,倒地就打呼噜,那时候站着也能困。
2021年10月17日,天气晴朗,高密作协一行10人到王吴水库考察水缘植物,开始的计划是从水库北岸沿大坝西头往西循水考察,到了之后发现这里已经开发成景点,得买票,不能随便进,我们只好临时改变计划,从大坝往东,经过杨家栏子村往南,再往西过王十字庄村到水库南岸。南岸的面貌基本还保持着水库刚竣工时候的样子,除了一块地方被沙厂挖掉一角,一块地方发展为苹果园,生态链还算完整。在青岛南天门风景开发区建设指挥部外面,就是王吴水库胶州提水站水渠附近,有几处四五米高的断面,裸露着大小不一的砂砾,基本不见土壤,表层已经长出不同品种的野草,几朵小黄花在秋天绽开着,左摇右晃。我在给野花野草拍照时想,这些砂砾可能来自五十多米深的水底,或者从很远的北岸运来,说不定还有我母亲挖的。如今,聪明人开始和想开始圈起来卖票了。
2
2009年,母亲六十八岁,中风快十个年头了,右侧手脚越来越不利索,在白杨叶子开始“唰唰”响的春夏之交,我们一大家子带着母亲去了一趟王吴水库。那年我对王吴水库还没方位感,不记得见过大坝,落脚的地方可能离大坝比较远,但离水库水面不远,是在一个高坡上,全是细沙子,沙地生了绿植,还没疯长,视觉很舒服,人在树底下,我记得多数是白杨,少数几棵刺槐,不密集但高大挺拔,水面的风吹过来,还有点凉意,是那种快乐的清凉。
母亲不能下到水边,也没法到处走,所以我们选择这个高坡,放好马扎,她坐着便可放眼水库,听听鸟叫,遥望水面。我不记得她说过什么话,似乎什么也没说,神情倒很专注,或许想起了她十七岁来挖水库的热火朝天的场景,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一幕幕还清晰吗?回到某个曾经熟悉的地方,记忆往往首先返回过去,然后再比较与现在的不同,然后再有混合的滋味泛起,然后再有必然的忧伤,仿佛来自生命的本能,起码我是这样的。
因为了解母亲的这段经历,当时我是有一些触动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夏问孔子三句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像画画一样,总要先有个洁白的底子,然后才能绘出漂亮的画。十七岁就是母亲那洁白的底子,因此到了八十多岁她依然可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洁白的底子就是善,有了善良,子夏才能言“礼”,孔子才能说“仁”。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一年多了,此时此刻,我该说点什么呢?诗云:“天高不可测,鹪鹩在沧浪。”
3
王吴水库在1958年4月6日动工兴建,上阵民工少的时候3万人,最多的时候8万人,来自高密和胶县两地,在昌潍专署组织下联合施工。当年7月24日,水库竣工,仅用时三个半月,一个流域面积344平方公里的中型水库就建成了。
我初次到王吴水库是2009年的春末夏初,陪当年8万民工之一的母亲。五十年后她第一次见到亲自挖过的水库灌满水的样子,后来我知道也是最后一次。她坐在碧幽幽的大水边的沙丘上,听着白杨树叶抑制不住的喧哗,盯着她的过去,一个不满十七岁的高密大嫚用尽全身力气铲起一锨黄泥,水渍渍的,准确地撇进两米开外手推车的长篓中,手心血泡的血水又沾到铁锨的腊干木柄上,她咬牙坚持着,继续那个机械性的挖土的动作。我也盯着那片自己的目力无法望到边际的水域,像盯着马尔克斯的羽毛笔在一张粗糙的黄皮纸上写下的一行潦潦草草的字:“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闪现高长荣译本的同时,范晔的译本也回旋于脑际:“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一刻,我没感觉滑稽,因为都是“那个遥远的下午”,内心只有对“多年以后”的敬重和肃穆。那两本《百年孤独》从1984年到2011年相隔27年,基本接近我离开高密在外地工作的时间,2009年在王吴水库边的那个下午我准确预见了《百年孤独》将又一次在2011年6月诞生。最为紧要的,我想起或预测到“那个遥远的下午”的时候对正在出神的母亲没有一丝不敬仰。
“东西也是有生命的,”吉卜赛人用刺耳的声调说,“只消唤起它们的灵性。”霍·阿·布恩迪亚狂热的想象力经常超过大自然的创造力,甚至越过奇迹和魔力的限度,他认为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可以用来开采地下的金子。
说来连自己都不信,除了陪母亲的这一次,后来的那些年,我竟然又连续去王吴水库多达5次,以我喜新厌旧的性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确实破了自己的例。以我到王吴水库准确的时间为证:2014年4月9日上午,2015年8月19日中午,2016年1月14日下午,2018年5月23日中午,2021年10月17日上午。从2014年到2021年,跨度只有短短的7年。
五次的印象各有鲜明之处。最鲜明的是水,准确说是水的变化,当然也有其他,比如首批建筑物,至今难忘。2014年4月9日我来的早了一点,大雾还没散,库区呈现朦胧状,我抹一把脸,并未湿漉漉,我放心了——相机被雾水包围,我担心它拒绝工作。它没拒绝工作,而且拼命咔嚓,我很感激。那个在西放水洞南百米处坐着挥杆钓鱼的,背对我,一动不动,水在动,鱼在动,风在动,他却不动,那份不动的魅力,让我不敢靠近。如果我靠近,我就要动,那么我就和水、鱼、风没什么区别了,为了不一样,我必须不动,但是我不动,就又和钓鱼的一样了,我不想和钓鱼的一样,因为我不喜欢钓鱼和钓鱼的,因此我动了我的一部分,只为了区分开动和不动,我让自己的脖子动,虽然带着脑袋也动了,那仅仅属于一种关系,可以忽略不计。我的脖子由西向东转动,绕过了南边,最后停止在东边。这时候刚好雾散了,水库长1376米的主坝前,就是水库前坡,大水55.26米高,而最大坝高只有14.4米,还差一米多水就漫过大坝了,我非常着急,想招呼钓鱼的赶紧顺着放水洞跑掉,顺便打开闸门泄水,可他还一动不动,因为我被惊呆了,嗓子哑了,没能喊出声。
2015年8月19日中午十二点左右我直接从大坝南坡下到了库边。坝坡的大块花岗岩成比例地沿着一个角度铺向库底,我的强力胶皮鞋踩到上面,产生无比强大的摩擦力,我都可以垂直在斜坡上往下走了。我像个一字垂直于花岗岩上,与库底保持平行,我闲庭信步地到达库底,竟自然而然地直立到地面上。我举起相机搜寻我曾经见过的55.26米高的大水,希望凑近了观察它们的相貌,可是我白忙活了,相机里不仅不见大水,连小水都很少了,远处有一点,一群野鸭子仿佛在脸盆里戏水,动作很挣扎,不像戏水,而像戏泥,泥巴里加了一点水而已,像我母亲在地瓜面里加了一点水一样然后拼命地搅和它们以便让地瓜面黏合在一起这样可以捏成地瓜面窝窝头就像她在工地每天吃的那种。泥巴边上站着几只白鹭,都在练习单腿站立,我知道它们想尽快适应旱地上的一条腿生活。白鹭不屑与野鸭为伍,其实是不屑与污泥为伍,白鹭爱干净,但在白鹭知识的边界,它们不知道污泥也是干净的,否则泥鳅怎么会喜欢在污泥里旅游?这就充分证明了污泥的干净程度不亚于水,因为泥鳅和鱼都是生命。白鹭认为污泥不干净的原因是为了让污泥证明自己干净,所以它们喜欢站在污泥一旁观察,它们并不知道这样的证明反而证明了自己不属于生命范畴,至于应该归它们入哪个范畴得问上帝,我说了不算,所以我收了相机抚摸身下的一种叫千金子的野草并且采集了一大把。千金子高到我大腿。它们本应该长在旱地的,现在挨挨挤挤长在库底,一望无际,我想它们也许知道我要来水库的缘故。它们的顶部在一夜之间结满了籽粒,为了表达对我的欢迎,我无比感动。因此,我要离开水库时,留给它们一首叫《千金子清晰》的诗,因为我是诗人,诗人就应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这种随地大小便非常受欢迎,像欢呼李白来了,我不慌不忙写下这首诗,方便白鹭或者野鸭没事的时候集体朗诵着表演,同时又方便想起我曾经来过想起大水想起水库想起石头想起墙垣想起河流想起村庄想起母亲:
稍远点的河流
并非由于远模糊
因为一滴雨水挂于眼睑
近处的千金子
并非由于近清晰
因为泪珠和咸味正好滚出眼眶
掐断几根千金子
河床草甸上著名的野草
举高到自己眉目间
它的穗叶,忽闪更多亮光
于是那个中午
便有了与其他中午不同的侧面
因此我看见了风
它携带为洗刷空旷修剪的羽毛
还看见光阴忽明忽暗的镜像
扫过我的指甲
至于那段距离中
尝试着陆的雨点
因为凝视而片刻迟缓
已经模糊的对岸
起伏的曲线比之前远
云降低高度,躲进了流水
浸水的身段比之前轻
几只白鹭原地踏步
它们现在不是白鹭而是几个
迷离的圆圈
于是我在那儿睡着了
高举一把千金子
像虚化的野鹤单腿站立
只剩手中的草,表情清晰
摇晃孤独而温柔的脸
2025年1月15日,1月24日草稿
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修改
作者简介:李言谙,笔名阿龙,山东高密人。作品散见《山东文学》《星星》《美文》《朔方》《当代人》《时代文学》《青岛文学》《海燕》等文学期刊。代表作散文集“老家三部曲”包括《发现高密》《夷地良人》《五龙河》,诗集“旷野三部曲”包括《枯之诗》《泥之诗》《药之诗》等。作品入选重要文集。获齐鲁散文奖、风筝都文化奖。
新著《心灵的归处》日前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精选了作者在济南、青岛、武夷山、建阳等地游学期间的创作,包括对家乡高密的记述和部分文史随笔,共三十篇优秀作品。已在当当网、京东购物等主流渠道发售,欢迎了解详情。
(全文3950字)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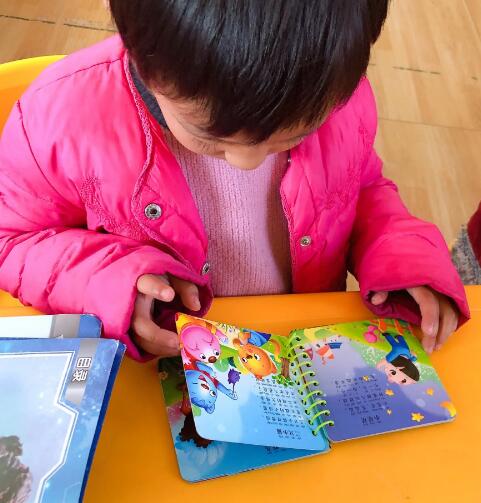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