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谁没做过梦?离奇古怪的梦,斑斓多彩的梦。
有的梦给人慰藉,温和而幸福;有的梦给人恐怖,悚然而悲凉……谁能说尽梦的曲折?谁能描摹梦的情境?
有一个阶段,我常常沉溺在梦中。一到晚上,想到即将可以拥衾而眠,进入纷奇纷杂多彩有趣的梦境,一股渴望温暖和走进海市蜃楼的探险般的奇妙,就涌入我心间。
也许那片梦境并不尽是美好的画面,会出现使我压抑、惊惧的场景,但我对梦的渴求,神秘的向往,恐惧和幸福的碰撞,并没有因此而衰减。
(2)
我常常想到达利的油画,有一幅名为《内战的预感》,画面是肢裂的人体横在天空,滴血的巨大的胳膊和腿下面,是如蚁的人群。
天空湛蓝,白云飘浮,巨大的不成比例的构图好似荒诞不经。但你分明被画面攫住了……战争,不就是给人这样残酷的感觉?
除了梦,你很难构思这样的图景,那是艺术家在终极处的跳跃,是梦与灵感的巧妙结合。
不仅绘画,诗歌、小说、电影等艺术领域,记梦、写梦、表现梦或者借鉴梦的特长搞创作,并成为特色和大师的,在世界艺术史上随处可见。
中国古代的司马相如梦作《大人赋》,受到了汉武帝的激赏;《凌波曲》是唐玄宗的“梦来之笔”,醒后抄下,竟丝毫修改不动;意大利著名作家莫拉维亚,在小说中写梦境可谓登峰造极,他的“白日梦”“梦中梦”“梦外梦”“梦非梦”,使真实与梦境交融一体,虚实难辨。你读他的故事,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恍若梦中的感觉,不知你是在读书呢还是在做梦。
也算天人合一吧。
还有马尔克斯、卡夫卡、奥茨、波特……尤其是卡夫卡,他简直是创造梦境的大师。在惊人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中,你已经不知不觉被领进梦的境地。
卡夫卡的《审判》《城堡》《美国》以及他大量的格言、寓言,无不整体笼罩着一片梦的氛围。然而它又是出奇地真实可信、打动人心。那些细节的场面可闻可触,历历在目却荒诞至极。
你不能不说卡夫卡抓到了现实与梦境的精髓,精彩地凸显了现代社会和人性的本质特征。
其实,中国在小说里写梦境早就有高手,尽管他那时也许还没有达到“形而上”的自觉程度。这个人就是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可以说是一部写梦的小说大全,由小说沿袭而来的许多成语如“一枕黄粱”“南柯一梦”等历久不衰。
“梦狐”“狐梦”等鬼魅故事具有的强大美学张力,至今令人感叹叫绝。只可惜没发现研究蒲翁“写梦”的专题文章,不能不说这是研究蒲翁的缺憾。
说到对梦的研究,最早、最有成效,并在艺术领域大显身手,拓展风采的,恐怕还要归到国外。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早在1900年就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从科学和医学的层面来说,这可能是人类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梦的理论专著了。
自弗洛伊德之后,在梦境的原野上耕耘的前仆后继如云而集,可以说一发而不可收。电影艺术大师伯格曼的《野草莓》,费里尼的《八个半》……纯粹是通过梦境来叙事抒情。
空荡荡的马路上,一辆载着棺材、无人驾驭的马车在行进,树上悬挂着一只巨大的钟表,钟表表面是软沓沓的,像皮革,弯弯地搭在树枝两头,而表针竟然还在走动!
仅单纯表现梦的荒诞是容易的,而在梦的画面中融人、情、事、理等密集信息量和美学要素,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有些大师做到了。
在长满了野草莓的山坡上,一个老人躺在暖暖的阳光下,他看到一个调皮的孩子,怎样在同其他孩子嬉闹,又是怎样在偷偷地爱慕着漂亮的表姐……场面的不断切换,使观众看到原来老人、孩子是同一个人,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暮年,被有机的梦境剪辑而成。
我看这个电影时,不知不觉间流了泪,被它浓浓的情思和伤感所打动。这个片子就是荣获戛纳电影奖的《野草莓》,主人翁也是导演伯格曼。
(3)
病理学家解释梦说,梦是人在睡眠状态中,大脑皮层一些部位没有休息,仍有程度不同的兴奋活动所致。因为是“植物性”的,所以不受人的理性控制。
这是从科学的角度讲,难免有些枯燥。我对梦,只是充满了大量的、不计其数的“亲历性”感受。
我不知是不是曾钟情小说创作,经常构思故事,痴迷其中,日萦于心,所以夜积成情的缘故,我的许多梦具有较完整的情节,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那情节与正常对照,还是有些支离破碎。你没法控制梦。
我随着抗日游击队去打伏击,日本鬼子的军车来了,朝我们藏身的破败的瓦房扫射……我们行车、娱乐,这时候,还有在抒情音乐中展开的爱情。我看见两个年轻女子在驻扎队伍的村边走着,一个剪短发的说:“你既然如此深切地爱他,那我就把他还给你……”另一个正在哭泣的女人,黑黑的长发遮住脸庞,低声说:“你还是把他带走吧,我愿孤独而死……”短发的也哭了,“姐姐,我确实离不开他啊……”
军号响起来了,缕缕声音把队伍牵进了天尽头的云层里,我却只顾安慰那位黑色长发的女人……
有的梦使我悲伤难抑,失声痛哭,有时会哭醒过来,胸仍然疼。再睡,却回不到先前同画面的梦里,情景变了,但内容依然悲伤。
我很惋惜那么多梦没有清晰地记住,也许不可能完全记住,否则人的大脑会因信息贮存太多而“爆炸”?
有的梦跨时间、跨地域,人物变换纷纭,背景跳来跳去,情节曲折复杂,不可捉摸。
有时尽管在梦中激动万分,醒来却如触摸一片影子,依稀朦胧,握不住那些斑斓的声音和图像。有时我就使劲回忆,以图再沉溺其中一会儿,再享受一下当时梦的情景。只可惜那门半开半掩,那地界虚虚实实,似真似幻,总找不到梦中真切的感受。
可能只要回头寻梦,总是味道不一样,不是“正宗”“原装”,梦的醇厚和魅力淡了、少了、浅了,这也常常使我早晨起来惆怅不已,倚坐床头,嗟叹而凄然。
(4)
有时梦中常出现令人尴尬的事和场面。
要上场进行篮球比赛了,我却找不到球鞋。在庄重的场合参加宴会,别人衣冠楚楚,我却穿一件背心,裤子污脏不堪。有时在梦中与持凶器的恶人搏斗,我的匕首却总像是橡皮做的,捅在对方身上,对方浑然不知疼痛,依然向我大打出手。有时我开枪,子弹打在敌人身上,敌人非但没有倒下,反而跳跃更加自如。我再狠扣扳机,子弹倾泻而出,但射中对方的子弹却“噗、噗”地从他身上往下掉……
我小时候还反复做从高处摔下来的梦。
有时那是一座相当高的楼,有时是悬崖峭壁,总之它高耸云端。我从那上面突然跌下来,耳边风声呼呼,“我马上就要粉身碎骨了!”恐惧勒紧我的心……我常常被这个梦吓醒。
有时我做梦在天上飞,鸟一样轻盈,自由自在,身下的河流、田畴、山峦、城市历历在目,我感觉到风鼓荡着肋下,不知是羽毛还是衣服。天高地阔,极目天舒,我盼望那梦别中断,别停下来……
(5)
有一些梦很怪,经常重复出现,许多年里五次三番钻进我的睡眠,例如,那个挥之不去的碗。
在部队当兵的时候,年轻力壮,能吃,一日三餐用的是大号的搪瓷碗,圆圆的,像个小盆。官兵们一律用白色布袋装碗,挂在连队食堂的墙上,像一排排倒扣的小瓢。因为部队非常讲究整齐划一,装碗的袋子是一样的,碗的大小也差不多,经常有战友拿错了,取出碗一看,碗的颜色、大小或筷子、汤匙不对,再在附近找自己的碗。
一次我外出集训回到连队,吃饭时发现自己的碗没了,打开一个布袋一看不是,再拿下一个扒开布袋口一看,勺子不对。这时吃饭的战友们排着队进来了,每个人径直走到自己的碗袋前,取出碗,把布袋仍旧挂到墙上,急急忙忙地去盛菜盛饭。
我沿着食堂看了一圈,墙上全是空空的瘪肚的白袋子,独独没有我的袋子。
战友们已经呼噜呼噜吃起饭来,我的饥饿感也呼噜呼噜在胃里响,焦急使我微微冒汗,眼有些花。
我记得我的袋子稍有些脏,副指导员曾提醒我:你的碗袋该洗了。
难道是连队嫌我的碗袋太脏给扔了?不会吧?要扔起码应该和我打个招呼啊。
我又找,确实没有。我只好到厨房里,向炊事班的战士说,你们谁先借给我一个碗用一下,我的碗不知怎么找不到了。
由于离开连队太久,炊事班有的战友和我不熟,继续在忙着。我听见我的声音带着哭腔,掺杂着委屈和失去饭碗的恐慌。没有碗,我拿什么盛饭?没有碗,我傻乎乎站在这里干什么?老天啊,没有碗我怎么吃饭!
炊事班的战士在大锅里炒菜,那大锅有咱们正常家里的锅好几个大,炒菜的铲子是一把铁锨,那一锅菜至少几十斤。锅里的菜味儿很香,我使劲闻了闻。挥动铁锨的战友站在锅前的台阶上,白色的热气笼罩着他,厨房里悄无声响朦朦胧胧。
借个碗给我用用吧,我饿坏了。我嘟囔着,有一个炊事员努努嘴,哦,墙角有个搪瓷大碗,里面还有一个小铝勺。
我赶快拿过来,这个碗很脏,看颜色不是我的,不论谁的,先吃饭再说。我跑到水龙头下反复用水洗,碗里黑乎乎的油污洗不掉,手上倒沾了些黏糊滑腻的油。那把铝勺也脏,整个被酸腐蚀坏了,勺面坑坑洼洼,还有小米般黑色的圆点,我反复冲洗,还是洗不干净。
我知道这小勺买新的才五分钱一把,只是现买来不及了,凑合使吧,我抓了一把碱,在小勺上搓,哎,这个管用,把小勺洗干净了,我又用碱面搓搪瓷碗,用清水冲洗完了,我赶快去食堂盛饭盛菜,结果到原先放着大盆饭菜的食堂一看,盆里的菜没了,只剩一些黑色的酱油汤,放馒头的大筐空空如也。
没饭了!没菜了!你来晚了,为了找饭碗,你耽误了饭点儿,饥肠辘辘活该倒霉。我手哆嗦着,到处找吃的,厨房里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不见了,我捧着刚刚洗出来的大碗,呆呆地站在冰凉的灶间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就在这时候,梦醒了。
我很奇怪,关于找不到碗的梦,竟然做了许多次,大同小异,每次都是心急如焚焦头烂额,这是什么原因?
按中国古人解梦的说法,日有所思,夜有其梦,可我从部队回地方若干年了,大部分时间是坐在摆满七碟八盘的酒桌旁,根本不会去想什么搪瓷碗的事儿,唉,那梦真是空穴来风,毫无征兆突如其来。
也许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有一定道理,“饭碗”的意象反映了我当年潜意识里的某些焦虑,顽固的如影随形。刚当兵我就四处奔波,打篮球、打排球、搞田径、搞报道,原本有户口的“籍贯”连队徒有其名,吃饭的地方不断变化,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还有机关、地方、野外,居无定所,蜻蜓点水无根浮萍,我在梦里找不到自己的碗,实属正常。何况,梦中的饭碗还带着象征意味:你的工作、业务固定了吗?你被借调来借调去,属于你的饭碗到底在哪里?
写到这里,我暗暗祈愿饭碗的梦就此消失,那些找碗焦虑别来骚扰我了,我也不想就碗的梦境深挖下去,那实在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啊。
(6)
梦是预兆?梦是谶言?
我常常在陌生的场合突然有“好像来过”“非常眼熟”的感觉,努力回忆,除了在梦中,别无他解。这使我好生奇怪。
已逝的台湾作家三毛曾记述过她一些后来被验证的梦。
她在一个从未去过的国家,遇到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子,车站的台阶是多少层,怎样拐弯……她历历在目。不可思议的是,她某一年到一个国家,一下火车,发现眼前所见竟然同她曾做过的梦一模一样!这是她第一次到这里来呀,这是怎么回事?她心惊胆颤,回忆着那个曾经做过的梦,想象着下一步可能出现的场面,果然,拐角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出现了,红衣服女人说的话,同三毛曾梦过的话毫厘不爽!三毛说她当时战栗不已。
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梦同未来是什么关系,梦是否有“预报”和因果作用,这就不得而知了。从古代许多记载来看,因果关系是有的,好像是“报应”或警示。
特别是一些文学作品,常写到阴间阳世,那梦无不给人提示、说明着什么。
真要如此,那我曾做过的大量关于战争的梦,大片大片的飞机,一步步紧逼而来的全副武装的敌人……出现的话,那将是多么恐怖的事儿!
(7)
梦为心声,此话不假。
想当初我爱好文学,舞文弄墨的开始阶段,梦中出现最多的是印成铅字的文章。一篇篇稿子投出去了,心也跟着到了遥远陌生的编辑部。天天期盼“发表”的消息,真是日绕夜萦。
编辑部的信封比一般信封都大,而且是牛皮纸,下边印着红或蓝的报刊名字。那信封常常飘进我的梦里来,有时许多天都接不到投稿的反馈,那梦中的反应更强烈了,大信封一个个像鸽子,缓缓飞来,落在我的手上,信封有的很厚,不用看就知道是退稿;薄薄的信封来了,十有八九是“用稿通知”……我的心颤栗着,那股焦灼后的喜悦涌遍全身……
还有关于杂志的梦。那些年公开发行的杂志极少,文学类杂志更是凤毛麟角。那时候书报亭也少的可怜,走遍一座城市,只有零星的书报亭。我常如饥似渴地趴在书报亭窗上,反复吞咽里边悬挂的几本可怜的杂志。
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书报亭四面的窗里挂满了各色各样的杂志,五颜六色,光彩夺目,《收获》《萌芽》《星星》《现代作家》《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延河》……我想抓这本,又想拿那本,眼花缭乱,目迷神移,眼睛恨不得像铲土机一样把那些杂志全铲到我怀里。
可惜,眼前的书报亭总是孤孤零零,灰不溜秋,里面点缀般地放着三两本杂志,封面又总是呆板单调,毫无生气。
由渴望产生的梦折磨着我,第二天我恹恹无神,总回想那些光彩照人的杂志,只可惜它们全是梦影!
后来“四人帮”倒台了,文学艺术界繁荣起来了,各种文学期刊纷纷复刊、创刊,书报亭也多了起来,而且果真与我梦中的情形,一片片绚丽目不暇接,我在梦里想到的杂志,不仅全出来了,而且多不胜数。
可是,我那些火烧般的热情已经锐减,“目”不再眩,“神”不再迷,面对那些形形色色的杂志,读读里边我开始挑剔并认为“一般化”的文章,心渐渐地冷了下来。
想到那些曾深切地折磨过我的“杂志梦”,我真为自己哀伤。
(8)
经常在梦里回到老屋。
妈妈去世多少年了?我似乎记不清了,那时候爸爸已经死了,老屋四面漏风,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妈妈经常为一顿顿的饭发愁。
我当兵以后,把省下来的津贴费,一分不剩地拿回家里,尽管杯水车薪。
退役回青岛后,我住单位的单身宿舍,可总挂念着母亲,抽空就往家里跑。
后来铁路宿舍遇到了拆迁,我们家的房子终于改善。就在拆迁的过程当中,母亲去世了。
她生前不止一次地说,只要你们能住上宽敞点的房,我就放心了。
我无数次在梦里往老屋跑,看到家里住上了宽敞的房子,非常高兴。那个住房好像还在老宿舍里,已经改造了,高大,多了几间。我问弟弟,妈妈呢?弟弟说,妈妈在外面看车子,还没回来。
有时候我在梦里急忙三火,一定要赶回家吃饭,让妈妈高兴。可是公交车迟迟不来,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好像有了传呼,可是打传呼也挺麻烦,你要找公用电话回复。我眼看着天色晚了,撒腿往家的方向跑,气喘吁吁,心跳如鼓,腰酸腿疼。终于到了家里,天已经黑了,我说,哥哥弟弟,我给你们带来了吃的,咱们坐下来,都吃点。
我看到在已经扩大的房子里,一个弟弟在另一间睡了,妈妈在稍大一点的屋子里,坐在炕上,默默垂泪。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还不睡?妈妈说,明天,咱们吃什么?再去借点钱吧,买点地瓜干,还有点苞米面,凑合一顿。
我哭醒了,为在梦里追不上公交车,回家晚了,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一种穷困潦倒的焦虑,为我给家里出不上力,伤心,难过,心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痛。
梦里的家啊,总是罩满忧郁和沉重,那些情景一次次缠着我,泪水把过往的岁月,打湿,浸透。
(9)
前不久的一个凌晨,我朦朦胧胧将醒未醒时,脑海突然跳出一句话:人生如梦,梦如人生!
我感到很惊奇,很新鲜。继而一想,这不是古今中外人们挂在嘴边说了若干朝代、若干年的一句丝毫不新的话吗?
2025.9.24
杜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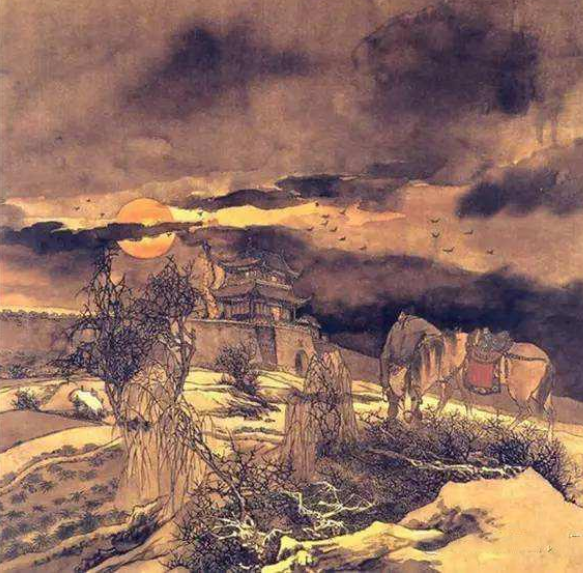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