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并未引起对古典诗词的重视,因为教育界鲜有人认识到:“古典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厦上的皇冠”!
更没有人重视:“中国的古典诗词是对人类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是东方艺术中永不衰败的奇葩!”
——这是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向西方人特地作出的庄严介绍。
现代美学家、文学理论家朱光潜在其代表作《诗论》中有言:“中国能拿出手去与西方文学比画比画的,只有古典诗词”。
——这是金玉良言。
但是欣赏古典诗词最重要的一点,被讲古典诗词的专家们都忽视了。之所以忽视,是因为他们都不懂、不知道、不重视欣赏古典诗词是在吟诵中开始,又在吟诵中结束的。
古代人欣赏古典诗词没有不吟诵的!为什么非要吟诵呢?
吟诵是欣赏古典诗词不可替代的欣赏手段。换言之,不会吟诵,则不会欣赏古典诗词。这在黄遵宪以前是家喻户晓的常识。连农夫村姑都知道:“诗是用来唱的!”所谓唱就是吟诵。
在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的古典诗词都表达了作者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在诗词的字义与声调混为一体共同营造出来的情调中体现出来的。
强调古典诗词涵有的情调,是近年研究古典诗词中的重要发现。这个发现是从隋唐人“为什么认为格律体是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受到的启发:格律体才有的音乐性声调,实质上就是为了配合诗句字义营造诗词的情调!
例如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从字义看,前两句平铺直叙毫无诗意、诗味,更无诗风!其实都是为后两句做的铺陈。后两句的字义才有了动人的情致。但是若吟诵中欣赏这首诗,前两句便可以从抑扬顿挫的声调发出字义所没有的感叹中的情调。
第一句吟诵中的“铁”是高声调唱到“消”字时,声调下滑出一种诗句字义难以表达的感叹!这种感叹到第二句便在声调中下抑为无可奈何的情调了。在无可奈何的情调中又攀升到高音调时,第三句的字义便有了惊世骇俗的力量。这种毋庸置疑的力量,推出的末句在低沉的声调中作出了可怕的假设,随着下滑的声调让读者感慨万千……
古代人欣赏古典诗词,都是沉浸在诗词的情调中与诗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是不会吟诵的今人难以达到的欣赏水平!
这几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的国学家,其实都是拿着前人例如杨伯峻的古文注释登台忽悠人罢了。你若问这些国学家:“为什么古代的散文中语气助词特别多”,他们没有人能想到古代的散文都是吟诵的。我不是国学家,但我研究古典诗词、古典散文中,发现今人的情感远不如古人的情感丰富深厚!不过 继续说下去是另一题目的文章了。
2025年9月7日
舟笠翁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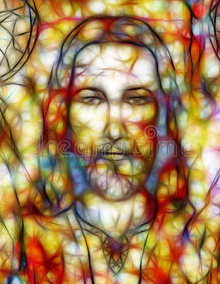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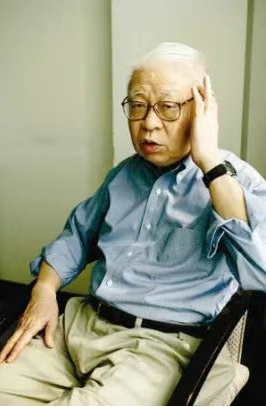


评论